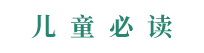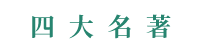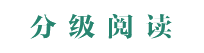二十四
觉新关心地看蕙一眼:蕙的脸上带了一种疲倦的神气,两只眼睛也不像从前那样地有光彩。他还听见她的一声干咳。他的心忽然跳得厉害了。他想说几句话,但是看见她的丈夫默默地坐在旁边,没有一点关心的表示,连看也不看她一眼,他便把话咽在肚里。他想世界上居然有这样的丈夫。但是他很有礼貌地顺从了蕙的意思,在蕙坐过的凳子上坐下来。他一面抓牌,一面暗暗地倾听蕙的脚步声。
觉新虽然在打牌,心里却想着别的事情。他时常把牌发错,使得在旁边看牌的周氏惋惜地说:“你怎样打这张?你该打那一张。我看你今天的打法有点不对。”觉新也不作声,依旧“心不在焉”地打下去。他的牌风本来不好,这样一来变得更坏了。加以坐在下手的郑国光(蕙的丈夫)因为吃不到觉新的牌,不时叽哩咕噜地抱怨着。觉新更觉得没有趣味,勉强打完这五圈。他一算不过输了八元几角,站起来想不打了。
但是蕙还没有回来,众人又不肯让他休息,逼着他坐下再打。
觉新打了两牌,蕙来了。她立在觉新身边,看他发牌。觉新知道蕙在旁边。发牌便稍微仔细一点。这回觉新在庄,国光坐在对面。他做好了“三翻”等着“西风”来和牌,觉新却扣了一张“西风”不打出去。后来周氏和了。觉新把牌倒下来。国光看见那一张孤零零的“西风”,非常不高兴,鼻子里出气哼了一声,恼怒地自语道:“真正岂有此理。一张孤零零的‘西风’做什么不打?我就没有看见这种打法。”周老太太惊愕地瞪了国光一眼。觉新把眉头微微一皱,脸色开始发红了。但是他仍旧装出不曾听见的样子一面洗牌,一面跟周老太太讲话。
蕙听见她的丈夫的话,她马上变了脸色。她埋下头过了片刻。她再把头举起时脸上却带着微笑。这是勉强做出来的笑容。她带笑地对觉新说:“大表哥,我给你打两牌。”
觉新想不到她会说这样的话。但是他马上明白了她的意思。他连忙站起来,让蕙道:“好,我‘手气’不好,就请你给我打罢。”
蕙坐下。觉新站在她的旁边。她发牌时常常掉头征求觉新的意见。觉新总是点头说“好”,偶尔也表示不同的意见。
他们这样地打了三牌。国光抱怨的次数更多了。觉新总觉得国光的眼光就在他同蕙的脸上盘旋。有一次他抬起头去看国光,同那个人的眼光碰在一起了。他觉得一股妒嫉之火在他的脸上燃烧。他不能忍受,便借故离开了蕙,走出了左厢房。
房里有点闷热,外面的空气却很清爽。天井中间横着一条宽的石板路,两旁的土地上长着两株梧桐树,给两边厢房多少遮了一点阳光。蝉声从树上传下来,那些小生物断续地叫着。觉新站在阶上觉得心里很空虚。房里的牌声和树上的蝉声聒噪地送进他的耳里,增加了他的烦闷。他立了片刻。国光忽然在房里发出一声怪叫,好像是谁和了大牌了。接着是蕙的一声轻微的咳嗽。觉新不能够再听那些声音。他便往左上房走去,他想找一个人谈几句话。他想起芸,他要去看她。
杨嫂站在左上房门口。她正要出来,看见觉新,便招呼一声:“大少爷。”
“二小姐在里头吗?”觉新顺口问道。
“在里头。我去给大少爷报信,”杨嫂讨好地说。
“好,难为你,”觉新感谢道。
杨嫂走了两步又站住了,她想起一件事情便回来对觉新低声报告道:“大少爷,我给你说,大小姐有喜了。”
这是一个好消息。然而说话和听话的人脸上都没有喜色。
觉新仿佛听见什么不入耳的话,皱起眉头沉下脸小声问道:“那么姑少爷待大小姐该好一点罢?”
“好一点?他们那种刻薄人家哪儿会做出厚道的事情。”杨嫂把嘴一扁,轻蔑地骂道。“他们只要少折磨大小姐就好了。
偏偏那两个老东西名堂多,今天一种规矩,明天一种规矩。姑少爷就只晓得耍脾气、摆架子。昨天家里有客,大小姐人不大舒服,没有下厨房做菜。后来亲家老太爷说了闲话,姑少爷晚上还发过一顿脾气,打烂了一个茶碗,叫大小姐哭了一场”“这些事情你对老太太她们说过没有?你最好不要告诉她们,免得她们心里难过,”觉新不加深思,担心地问道。
“我已经对太太说过了,”杨嫂愤慨地说。“我也晓得太太她们没有法子。不过倘若把这些事情瞒住太太她们,万一大小姐日后有三长两短,我怎么对得起太太她们?”杨嫂说到后面,她的眼圈也红了,便不等觉新开口,就往芸的房间去了。
“有三长两短,”这句话像一柄铁锤在觉新的脑门上打击了一下。觉新痴呆地站在房中,过了半晌,才辩驳似地说道:“不会的。至少将来小少爷生出来,大小姐就可以过好日子了。”他说完听不见应声,觉得房里很空阔。他惊觉似地四下一看,才知道他正对着这个空屋子讲话,杨嫂已经不在这里了。
芸听说觉新来看她,十分高兴,不等觉新进去,便走出来迎接。觉新跟着芸进了她的房间。芸让他坐下,递了一把团扇给他,一面问道:“大表哥你不是在打牌吗?输了吗,赢了?”
“输了八块多钱。现在蕙表妹在替我打,”觉新拿着团扇客气地答道。
“可惜我不能够出去,不然我替你打,一定会赢钱的。那天不是赢过一回?”芸微笑地说,两只眼睛天真地望着觉新,粉脸上明显地现出一对酒涡。
“芸表妹,你一个人关在屋里真乏味。如果你姐夫不来就好了,”觉新无意地说。
“真讨厌。从前还好。现在姐姐来一趟他总要跟一趟,来了又不肯走。要是留姐姐多住一天,他很早就打发人来接。大表哥,你看这种人还有什么法子可想?”芸收敛了笑容,噘起嘴,气愤地说。
觉新想了一想,然后说:“最好把蕙表妹请到我们家里头去耍。你也去。我们不请表妹夫,看他怎么来?”
芸立刻开颜答道:“这个法子很好。”但是后来她又皱起眉头扫兴地说:“他不会让姐姐去的。”
“那么也就没有别的法子了,”觉新失望地说。
“其实姐姐也太懦弱。姐姐又不是卖给他们郑家的。看亲戚,走人户也是常事。这也要听他的话。”芸忿懑不平地说。
“芸表妹,你留心过没有?你姐姐近来很憔悴,常常干咳,好像有病似的,”觉新忽然带着严肃的表情低声问道。
“大表哥,你是不是说姐姐有肺病?”芸惊恐地失声问道。
“也许还不至于。不过她平日应当高兴一点才行,心境是很重要的,”觉新担心地答道。
“姐姐在他们家里哪儿还会高兴?只要不被他们一家人气死就算是天保佑了。姐姐的心境我是晓得的。”
“然而我们总要想个法子才好。现在没有肺病,将来也难保不会有。她应当好生将息。芸表妹,你多劝劝她也是好的。”
“唉,单是空口劝人,有什么好处?如果我处在姐姐那样的境地,我也很难强为欢笑。何况姐姐又是生就多愁善感的。”
蕙的声音突然在房门口响起来。她走进来就问道:“你们在说我做什么?”
“我们并没有说到你,”觉新连忙抵赖道。他又问:“蕙表妹,你没有打牌了?”
“我听不惯他那种叽哩咕噜,我交给妈去打了,”蕙埋下头迟疑半晌才低声答道。
“姐姐,我看你也有点累了,多歇一会儿也好,”芸知道蕙心里烦恼,便亲热地安慰道。“我跟大表哥正谈到你。大表哥喊我劝你好生将息……”蕙苦涩地一笑,含着深情地看了觉新一眼,感谢地说:“多谢大表哥关心。”过后她又埋下头说:“刚才他那种话请大表哥不要介意。他本来是那种人,大表哥自然不会跟他一般见识。”
觉新微微一笑,但是这笑容掩盖不了他的痛苦的表情。他说:“蕙表妹,你怎么跟我客气起来了?你想我难道会为那种小事情生气?”
“我也晓得的,不过那种话连我听见也厌恶,”蕙忽然呜咽地说。
“姐姐,你不要这样。你现在就这样爱伤心,以后怎么过日子?”芸爱惜地劝道。她站起来走到蕙的身边,摸出手帕给蕙揩眼泪。
“二妹,我哪儿还敢想到以后的事?我有许多话不敢在婆婆同妈面前说,怕她们听见了徒然惹起她们伤心,”蕙忍住泪悲声说。“我这两三次回来,在她们面前总是勉强做出高兴的神气。可是他偏偏要说那种话,做出那种讨人嫌的样子,叫人忍受不住,他刚才得罪了大表哥,幸亏大表哥不计较。要是换了像他那样的人,就会生气了。”
“蕙表妹,这种事情还提它做什么?”觉新勉强做出平静的声音打岔道。“我倒有一件正经事跟你商量。二妹、三妹、还有琴妹,她们要我做代表,请你哪天到我们家里去耍。你自从出阁以后,只到我们家里去过一次,还是同你姑少爷一起去的。她们没有机会同你多谈话,很想念你。”
蕙的眼睛忽然亮了一下。她柔声问道:“二表妹她们怎样了?多谢她们还记得起我。她们都好罢。想起她们,我就好像在做梦。我一定会去的。不过……”她皱起眉头停了一下,才接下去说:“不过要看他什么时候高兴让我去。不然他发起脾气来我真害怕。”
“二妹、琴妹她们都好,”觉新刚说了这句话,芸就开口了。
“人家请的是你,又不是请姐夫,做什么要等他高兴?”芸气恼地插嘴道:她早在蕙的身边一个春凳上坐了下来。
“唉,二妹,你不晓得他是那种世间少有的古怪人。”蕙叹了一口气,诉苦道。“不过他还比我那两位公公婆婆好一点。
他们的花样更多。东一种规矩、西一种规矩,好像遍地都是刀山,叫我寸步难行。他们家里不请个好厨子,有客来总要我去做菜。从前是婆婆做。她说接了媳妇应当媳妇来做,如今该当她享福……”她摇摇头哽咽地说:“我说过不要说,现在又说了这些。话横竖说不完的。你们就忘了我这个苦命人罢。我实在——”这时杨嫂突然走进房来。她没有听清楚蕙的话,也不曾注意到蕙的脸上的表情,她揭起门帘便慌忙地大声说:“大小姐,姑少爷喊你立刻就去。”
蕙听见这话便在中途住了嘴。她并不站起来,却默默地用手帕揩眼泪。
“杨嫂,什么事情?”芸抬起头悄然问道。
“什么事?他输了钱心里不高兴,故意折磨人。倘若大小姐不去,他说不定会当着许多人面前发脾气。大小姐不晓得是哪一辈子的冤孽,才碰到这种怪物。”杨嫂咬牙切齿地咒骂道。她忽然注意到蕙在揩眼泪,连忙走到蕙的身边,吃惊地问道:“大小姐,你什么事情伤心?”
“我没有伤心,”蕙取开手帕,摇摇头说。
杨嫂不相信,惊疑地望着蕙。芸却在旁边说:“杨嫂,你好好地陪大小姐去罢。”她一面向杨嫂努嘴示意,一面俯着身子在蕙的耳边说:“姐姐,你去了再来,我们在这儿等你。”
蕙长叹一声,站起来,默默地跟着杨嫂走了。
芸和觉新悲痛地望着蕙的背影消失在门槛外面。房里只剩下他们两人。他们痴痴地望着门帘,过了好一会儿工夫,芸忽然悔恨地说:“只恨我不是一个男子。”
芸只说了这一句简单的话。但是觉新已经明白她的意思了。不过他想得更多。他以为芸在讽刺他。他想:我不是一个男子吗?我除了束手看着她受罪外,还能够做什么事情呢?
他开始憎厌自己,为自己感到羞惭了。他再不敢正眼看芸,害怕会遇到责备的眼光。其实芸丝毫没有责备他、讽刺他的心思。
过了一会儿觉新卸责似地搭讪问道:“蕙表妹的事情大舅晓得吗?”
“都晓得,”芸点头答道。“说起来真气人,大妈为了姐姐的事情跟大伯伯吵过两次架。大伯伯总袒护姐夫,说姐姐嫁给郑家做媳妇,当然要依郑家的规矩。做媳妇自然要听从翁姑的话,听从姑少爷的话,受点委屈,才是正理。大妈抱怨大伯伯没有父女的情分,这倒是真的。姐姐回来几次都没有看见大伯伯。倒是姐夫来见过他几次。大伯伯还出了题目要姐夫作文。姐夫把作文送来,大伯伯看了非常得意,赞不绝口,说姐夫是个‘奇才’。大伯伯同太亲翁非常要好,近来都在办什么孔教会的事情。……”“做父亲的原来都是一样,”觉新忍不住怨愤地说。他并不想说这句话,却无意地说了出来,原来他还想起淑英的事情。在对待女儿这一点上那两个父亲就好像是从一个模子里铸出来似的。觉新说了这句话,忽然想到芸也许不会明白他的意思,便加了一句:“我想大舅总有一天会明白过来的。”
“可是太晚了,”芸带了一点恐怖地说。
这一天周伯涛居然赶回家来吃午饭。蕙亲热地招呼她的父亲。他对她却颇冷淡。他倒同国光谈了不少的话。国光恭恭敬敬地点着他那大而方的头颅,应答着。国光总是顺着伯涛的口气说话,开口一个“爹”,闭口一声“爹”,而且“是”字更不绝于口,教伯涛听得十分满意。他在席上有两次一面夸奖他的女婿,一面瞪着他的木鸡似的儿子。他威严地对枚少爷说:“你听见没有?你能学到你姐夫一半就好了。”枚少爷吓得只顾低头答是。
蕙坐在周老太太的旁边。杨嫂在后面给她们挥扇。另一边坐的是国光。一个新买来的婢女翠凤立在他同伯涛两人后面打扇。蕙埋下头迟缓地动着筷子,她不去挟菜,总是周老太太、陈氏她们挟了菜送到她的面前。她勉强吃了半碗饭便放下碗。周老太太她们关心地劝她多吃。伯涛却仿佛没有看见蕙似的,只顾同国光说话。他的谈锋甚健,散席后他还把国光和觉新邀到对面他的书房里去。他对着觉新不断地称赞国光的文才。他从写字台的抽屉里取出国光的用小红格子纸誊正的文章,递给觉新看。觉新接过文章,看题目是:《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论》,不觉皱起眉头来。国光在这个题目下面,洋洋洒洒地写了三四千字。觉新“心不在焉”地看下去,看完了,连忙赞几声好。其实文章里面说些什么他都不知道。
国光吃过午饭后本来打算稍坐片刻时就回家去,后来听见别人称赞他的文章,他非常高兴,便多坐了一会儿,才告辞出来。他走出书房时,还央求伯涛给他出了一个新的作文题目。
觉新比较国光夫妇后走。他看见他们上了轿子。还在大厅上多站了一会儿。他觉得他是在梦里。一切都是空虚。他忽然想起一件事情:伯涛今天对蕙一共说了五句话。这个数目不会错,他仔细地观察以后记下来的。他惨然地笑了一笑。
他又从梦中跌回到现实里面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