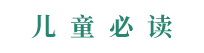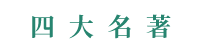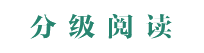热河省一个偏僻的山村里,住着一家姓李的人家。这家人家只有祖父和孙女两个。祖父老了,成天病在炕上,孙女秀妮就打柴、种地养活着祖父和自己。秀妮是个又漂亮、又结实、又能干的姑娘。村里的青年小伙子都想娶这个姑娘,可是秀妮长到二十一岁了,却谁也没有嫁。原因是她从十一岁就给人家当童养媳,后来到她十五岁上,她的“丈夫”死了,她才又回到祖父的家里。这婚姻伤透了她的心,而且为了侍养老祖父,她就不想很快结婚。祖父因为年老多病需要孙女的照顾,也不愿意孙女离开他,于是祖孙俩就相依为命地活下来。祖父爱孙女,闺女家有时送来几个粘饼子、腌鸡蛋,他总要留给孙女儿吃,自己只尝一点点。孙女呢,养种的地是地主的,交了租子只剩一把柴禾,为了叫老祖父喝上一碗热糊糊,她除了种地之外,一有空就扛着斧头上山去打柴;夜晚灯下给人做针线。村里人都赞美着这个勤劳、纯朴的好姑娘——这真是青年人梦里都想着的好姑娘。可是这么个好姑娘,在她二十一岁的那年冬天,厄运来了:住在北平城里的大地主林伯唐亲自下乡来收租的时候,秀妮忽然被他发现了。
他惊羡她的美丽,就要讨她当姨太太。虽然他已经五十多岁了,虽然他已经讨过好几房姨太太,并且还叫大太太徐凤英打跑过好几个从妓院里买来的红妓。但是他既然看上了秀妮,看上她这健康的带点“野味”的姑娘,那他就绝不会放手。为了镇压佃户的反抗,他是从热河督军汤玉麟那儿弄到军警来帮他收租的,孤弱的秀妮祖孙俩,哪能抵抗这强暴的力量!于是秀妮就在这小小山村里的二地主(庄头)家里,成了大地主林伯唐的姨太太。她哭过,她寻死过,她咬过林伯唐的手指头,但是这一切抵抗全无济于事,林伯唐捻着八字胡笑吟吟地还是把她弄到了手。
两个月后,秀妮怀了孕,林伯唐把她带回北平的公馆里来。老祖父就在秀妮离开村子的那天夜里,一个人颤巍巍地拄着拐杖跳到了村旁的白河川里。
秀妮到了北平的林公馆里,聪明、伶俐的姑娘变成了痴痴呆呆的傻子。成天一句话也不说,除了吃饭、做活,就两眼直勾勾地冲着墙发呆。徐凤英看在秀妮有孕的份上,开始对她还不错,因为徐凤英自己生过几个孩子,一个也没活,所以就希望秀妮替林家生个孩子。
秀妮生下孩子后,精神好了一些,她把全部的希望和爱寄托在孩子身上。她多么爱她怀里的白白胖胖的女孩呵!这孩子浅浅的一笑,能使她暂时忘掉了刻骨的伤痛,忘掉了耻辱的生活,给她生活下来的勇气。常常在深夜里,老头子林伯唐到别的姨太太房里去了,秀妮悄悄爬起身,给孩子换尿布、喂奶,亲着美丽的小圆脸蛋,然后一边哽咽着一边喃喃地说:
可是有一天,徐凤英喊来了秀妮,先把孩子接抱在手里,然后脸色大变,对秀妮说:“孩子是我家老爷的,我要留下她!你这不要脸的穷女人,现在就给我滚!” 秀妮惊呆了。接着大哭着,撞着头,拼命要夺回她的孩子。但是她夺不回来了!林伯唐玩够了她,早躲到一边去了。“妈!妈妈!要……”孩子在徐凤英手里张着小手,哭着要妈。秀妮却被几个如狼似虎的听差推搡着架上了停在大门外的汽车。
秀妮的孩子,林伯唐替她起名叫林道静。开始林伯唐夫妇还很喜欢她,后来当她三岁时,徐凤英自己也养了个儿子之后,小道静的厄运就来了:不断挨打,夜晚和佣人睡在一起;没有事,徐凤英不叫她进屋,她就成天在街上和捡煤渣的小孩一起玩。
一年冬天,有一天徐凤英不知为什么高兴了,把道静叫到屋里,和她说了几句话,看她一边呐呐地回答,一边不住地浑身乱动,她惊奇地揪过她来,问她怎么了。
“痒痒……”孩子只七岁,吓得吸溜着鼻涕要哭的样子。
林伯唐捻着八字胡,冲妻子笑着点点头:“好!太太从来都是眼力过人的。‘女子无才便是德’已经不大时兴了,叫她念念书也好。”
这么着,小道静被送到学校里去读书。她喜欢读书,人也聪明,可就是有点儿乖僻,一天到晚,一句话也不说,不知道的人还以为她是个哑巴。弟弟仗着母亲的娇惯,常欺侮她、打她,她可从来不哭。有时,她不理他,任他打;有时火气上来了,她就狠狠地揍弟弟几下子。当然这样她会招来更凶的一顿狠打。母亲打她不用板子,不用棍子,却喜欢用手拧、用牙齿咬。一个夜晚,道静已经在“下房”睡着了,弟弟打破了一个母亲心爱的花瓶,他却推在道静身上。于是道静在睡梦中突然被一阵剧烈的疼痛惊醒来,她立时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于是就咬紧牙关,顽强地准备着一切痛苦的袭来。
“狗娘养的!越来越胆大啦。赔,赔我的花瓶!”
她的小腿被拧肿了,胳膊被咬得透出一个个红血印。但是小道静不哭,不求饶,没有一滴眼泪从她倔强的眼睛里流出来。在这个家庭里,她就这样像小狗似的活下来了。家里所有的人里面,只有一个年老的佣人王妈关心她、心疼她,常常偷着照顾她。但是还不能叫徐凤英知道。道静当然也爱王妈,她肚子饿了,身上冷了,总去找王妈;她的眼泪也只当着王妈一个人流。
道静高小毕业考上了北平西郊的南山女子中学之后,母亲对她的态度有了显著的好转。因为这时她已经长成了一个颀长、俊美的少女。她的脸庞是椭圆的、白皙的、晶莹得好像透明的玉石。眉毛很长、很黑,浓秀地渗入了鬓角,而最漂亮的还是她那双忧郁的嫣然动人的眼睛。她从小不爱讲话,不爱笑,孤独,不爱理人。可是徐凤英并不注意这些,她注意的是这女孩子的相貌的变化,和如何使她具有一定的学历,因为这是那个时代的时髦妇女要嫁一个有钱有势的丈夫所必备的条件。
学校开学了,第一天离家去上学,父母亲高兴得亲自送道静到大门口去上车。林伯唐穿着纺绸长衫,摸着胡子站在大门口外的玉石台阶上,沉吟有顷,然后对坐在洋车上就要起程的道静笑吟吟地赞叹说:
林伯唐不仅是教育家、慈善家,而且是颇有名望的前清举人。他中举之后,还没等进京应考,正赶上康梁变法维新,北京办了个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的前身——原注],这位举人老爷就追赶着潮流,带了夫人,做了京师大学堂的“大学士”。到了民国,这位善于追赶潮流的“大学士”,又赶上了办教育吃香的时候,于是他很快成为教育家,借了“办教育”为名,向清朝王爷手里用低价买了大批“跑马占圈”的土地[清朝王爷骑马,马一气跑过的地方,由皇帝赏赐给他,即为“跑马占圈”的土地——原注]。于是戊戌举人、京师大学堂大学士、悯安慈幼院院长、务本大学校校长等头衔的名片,在煊赫的“上流”社会里飞舞起来了。人们钦佩着“才德兼备”的林伯唐教授,却没有人说他曾怎样残酷地玩弄了可怜的秀妮。
林伯唐熟读过四书五经,也研究过康德和孟德斯鸠,不过最使他醉心的还是科班出身的翰林学士。所以他对女儿啧啧赞叹她上了中学就等于中了秀才。
没等道静开口,母亲接着说话了。她是胖身子,八月里还挥着小绢扇。她眯缝着眼睛,也站在台阶上欣赏着女儿:“乖乖,好好念书呀!妈会想法子弄钱供给你上中学、上大学,要是留洋回来,那就比中了女状元还享不清的荣华富贵哩!”她说的好端端的,忽然扭头冲着老头子,鼻子哧了一声撒娇似的:“你老东西嘻嘻笑什么?女儿是我生的!我养的!她挣钱发了财,横竖没有你老东西的份!”
徐凤英溅着唾沫星子好像生了气,林伯唐反倒得意地哈哈笑了。他悠然自得地冲着妻子连连点头:“太太,归你!归你!什么全归你。连女婿挣的钱也全归你不好吗?”
十二岁的林道静厌恶地瞅瞅她的所谓父母亲,眼眶里浮着泪珠,一言没发,坐着洋车走了。
一九三一年,林道静读到离高中毕业只有两个多月了。一天下午,她从北平的家里回到学校后,神情惨淡地坐在课堂的位子上,半天功夫一动也不动。好些同学都奇怪地看着她,有人走过来问她:“林道静!你母亲叫你回北平什么事呀?怎么一回来变成这样啦?”
陈蔚如拉着她的袖子,摸着她的头发,温柔地悄声说:“林,告诉我,什么事呀?” 道静像段木头,不声不响地仍然呆坐着。同学中有些人哄地一声笑起来了,道静才像从梦里惊醒似的,揉揉眼睛苦笑道:“你们笑什么?少拿别人开心!”说完站起脚就走了。过一会儿,陈蔚如跟着她走到了学校西边的西河沟。两个女孩子紧挨着走。走着,走着,林道静突然站住身,回过头,愣愣地盯着小陈说:“小陈,我不能上学了!”说这话时,她的脸色异常苍白。
“为什么?小林,你妈叫你回去倒是怎么回事?”多情的女孩子,被她朋友的痛苦吓住了,她显得比道静更加惊悸不安。道静又不出声了。她们俩走到西河沟的树丛里,靠在河边的垂柳下。道静凝视着闪着金光的河水,半晌,才自言自语似的说:“家里破产啦——我父亲因为地权的事打了官司,闹得身败名裂,就把口外的地一古脑儿瞒着母亲全卖光,带着姨太太偷跑掉了。现在我成了我妈唯一的财产。”
“什么?怎么你是财产?你也不是钱呀!”
“我妈想叫我当摇钱树。她叫我回去,就为了叫我嫁个阔佬,她好依旧享福。我不答应,和她决裂了。”
“这怎么办呢?”陈蔚如捏紧道静的手几乎哭了出来。可是这时道静反而沉静地抚着小陈的手说:“小陈,别着急!反正我不屈服!最后不行,还有个死!”
接着徐凤英果然断绝了女儿的供给,她企图用这个办法威胁道静屈服。可是道静不屈服。她本来立刻就要离开学校去谋生的,可是暑假还不到,到哪儿去呢?有些热情的同学同情她,几个人每月替她凑饭费,她就这样勉强读完了最后两个月的书。
不久,到了放暑假的时候,她不得不怀着渺茫的希望和沉重的心情准备回家去。她知道如果母亲不能回心转意,她就不能再读书。而她是热望能够升大学读书的。可是凶狠的母亲会回心吗?她惶惑了。她除了喜欢文学也很喜欢音乐。此刻放了假,她雇了洋车从学校向城里拉去时,车上还带了一堆乐器——笙、笛、箫、月琴、二胡,她那最宝贵的蝴蝶牌口琴就放在口袋里。无论走到哪儿,她总是随身带着这一堆东西。因此同学们给她取了两个外号:好听的叫做“洞箫仙子”,不好听的叫做“乐器铺”。下课之后,她常常一个人吹着、弹着,这时候看见她的人,都有些惊讶她那双忧郁的眼睛忽然流露出喜悦的光芒,也只有这时候,她那过于沉重的神情才显出了孩子般的稚气。当然,这是半年以前的情况。自从她的生活突然发生了这意外的变故,她就不大抚弄这些东西了,因此有些同学笑着问她:“洞箫仙子,怎么不开乐器铺啦?”她淡淡地笑一笑,默然地走开了。
洋车在颠簸不平的土道上慢慢走着,她的心也一刻刻更加沉重不安。母亲上次对她那种凶狠的好像鞭打佃户时的恶煞神气,时时在她眼前浮动:“狗娘养的!娘老子养着你为了什么?”、“不孝的枭鸟给脸不要脸!不听话,给我滚蛋!”想到这里,她身上微微发抖,仿佛怕人抢去似的,她用力抱住了怀里的竹笙。可是当她下了车,走进母亲的房门,情形却出于她的意外。母亲正和客人打着牌,见她回来了,亲热地拉着她的手,笑吟吟地说:“姑娘,好女儿,你回来啦?路上热吧?今天客人不少,他们都在称赞你读书读得好呢!”
道静想:“妈妈也许不逼我嫁人了,也许还能供给我念书?”她一向认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要是还能读书,该是多么幸福呀。于是,她向客人们微微鞠了一躬——过去她是非常讨厌家里的赌客、烟客的,今天却仿佛看他们顺眼一些,竟站在牌桌旁,对他们羞涩地笑了笑。
“这位是胡局长,”母亲指着一个坐在上首的黄瘦的西服男子给道静介绍,“这就是小女道静。”她眯起肿眼向那黄瘦的男子恭顺地又像夸耀地一笑时,道静心里突然感到了不自在。于是她赶快扭转身子走到里屋去,再也听不到母亲后来又说了些什么话。
道静在家里住下来了,并且参加了师范大学的入学考试。她考试的成绩很好,心里很高兴。可是,一想到叫她结婚的那件事,再加上家里通宵不停的麻将牌声,轻贱的男女调情声,靡靡的歌曲声和输了钱的男人怒骂声……仍然使她一天比一天烦闷、痛苦。“没了男人,破了产,妈妈堕落成什么样的人了呵!”她看见四十七八岁的徐凤英,成天打扮得花枝招展,向男人献媚的丑态,心里又难受又讨厌。
半个多月过去了。这一天母亲好像分外高兴,带道静到店里买了一件白洋纱长衫、一双白帆布鞋。母亲一定叫她买漂亮的好衣料,可是这女孩子很执拗——在夏天她永远只穿短短的白旗袍,白袜白鞋,打扮得像个护士。母亲没办法,只好依了她。晚上,母亲又替道静烧了她最爱吃的菜。吃罢饭,连着弟弟小风,母子三人一块坐在床边说起闲话。正东拉西扯说得高兴,母亲忽然说:“静,你爸爸这老东西跑得没有影子了,地也光了;剩下咱母子们——你兄弟又小,你又还没学好本事,咱娘儿几个以后可怎么过活呢?”母亲说着流下眼泪,道静也低下了头。这时,母亲反而抚慰她:“好姑娘,不要难过,只要听妈的话,管保咱们有吃有穿,你也还能去上学。”
道静没有出声,母亲想了一下咬着指甲笑道:“呵,好姑娘,说实话,你究竟愿意嫁个什么样子的丈夫呢?”半晌没有回答。
“说呀,在问你呀!”
“妈,我从来没想过这些事——您不是允许我还去念书吗?我求您再别跟我提这些事了。”
母亲忍住火气,皱着眉头:“你说的没道理。娘老子十六岁就跟你爹结了婚。再说,结了婚也并不妨碍你去念书呀。”母亲说着从床上站起来,把两只肉眼泡眯成一条缝,拉着女儿的手笑道,“亲女儿,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常来咱家的那位胡局长,看上了你,喜欢你的才貌。局长从来没有结过婚,人不过三十多岁,可是个有财有势的阔人呢。”
看见女儿低着头不做声,以为女孩子害羞,肯了也不愿说。于是徐凤英高兴得眯着眼睛,笑着,滔滔地开了话匣子:“宝贝,你要同意了,福可是享不清的呵,局长在南京上海全有洋房;北平银行里存着大批现款;在家乡有一二十顷土地;上海还有不少股票
道静再也忍耐不下去了,她猛地甩掉母亲的手,发着沉闷的哭声:“妈,您别总打我的主意行不行?我宁可死了,也不能做他们那些军阀官僚的玩物!您死了这条心吧!”
母亲勃然大怒了。她跳起来,两眼露出可怕的凶光,青筋暴露的白手好像寻找着打人的物件在各处颤动。
道静好像泥胎一般呆在地上。母亲喊叫的是些什么话呀?自己的亲母亲是个什么样的人?过去她只知道自己的亲妈死了,因为不是徐凤英生的,所以受折磨。至于亲妈妈的事情她是一点也不知道的。
没有回声。黑暗闷热的小屋里死一般的沉寂。
“孩子,”还没出声,王妈也哽咽住了。她断断续续地说:“你,你还记着你小时候我给你讲的那个砍柴姑娘的事?那,那就是你那亲妈呀!”
孤苦无依的小道静,在冬天的长夜,常常偎在王妈的怀里,听她讲许多许多动听的民间故事。其中,也讲到过秀妮的故事。但是她不敢违背徐凤英的命令,没有说出那个砍柴的、被地主逼迫做了小老婆的姑娘就是小道静的妈妈。现在,善良的老妈妈,再也忍耐不住了,于是告诉了道静关于秀妮的全部故事。
秀妮自从被林伯唐夫妇指使人架上汽车,就被当作礼物送到林伯唐的一个朋友家里。可是秀妮疯狂地冲出了那个朋友家的大门,跑到林家来要孩子。林公馆门禁森严,进去不得,她就披头散发,跌跌撞撞,不停地围着林家的院墙转;不吃不喝、成日成夜来来回回地转。一边转着,一边悲惨地号叫:“还我孩子!还我孩子!你这丧尽天良、狼心狗肺的人,该千刀万剐的人呀,还我孩子!还我孩子……”
林伯唐看她闹得太厉害,实在有损大学校长的尊严,就命人绑架着,把急疯了的秀妮送回了白河川旁的山村。一回到故乡,一望见故乡的山和水,人事不知的秀妮似乎明白一些了,能讲两句明白话了,也知道哭了。她想,孩子虽然不能再见,但总还可以和老祖父
道静倒在王妈的小铺上,瘫软得好像失掉了知觉。半天,她才勉强坐起来,用冰冷的手指紧紧捏住王妈枯瘦的手,低低地喊了一声:“妈妈……”
“孩子,别哭啦,叫你妈听见不是玩的!”王妈劝道静别哭,自己却擦着眼泪。
“王妈妈,我再也不怕他们了……我要离开这个家!”过了一会儿,道静从王妈的床上跳起来说。
“上哪儿去?”王妈吃了一惊,又扯着衣襟擦起眼泪来。
“回学校。”道静改了口,“在学校住些天,等师大发了榜再回来。”
“回学校?那好。千万可别乱跑呀!娘儿俩吵几句嘴,不要紧,几天就过去了。孩子,既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啊。”老太婆嘴里一边叨叨,一边划了根洋火到枕头底下摸摸索索地寻找起什么来。道静在鱼白色的晨光中望着她,想说的话到了嘴边还没出口,老太婆已经找到了一个小小的纸包。她小心翼翼地慢慢地打开它,叫道静又划了一根洋火,照出几张花花绿绿的钞票来。她仔细地数了数这些钞票,然后珍重地放在道静手中,声音有点儿沙哑:“这是你妈才给我的两个月工钱——十块钱。好闺女,你拿回学堂交饭钱去吧。忍耐着点,缺个什么就跟我要。唉,命苦的娘俩
道静接过钱来,哽咽着:“趁着他们睡觉,我走啦。我,我不是——王妈妈再见!”一霎间,她眼前站着的满脸皱纹的老太婆,忽然变成一个美丽憔悴的少妇。她披散着头发,流着眼泪,绝望地哀嚎着“还我孩子!还我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