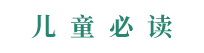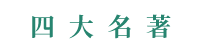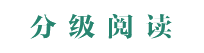十月初,林道静改名路芳,离开了刘大姐,以巡视员的名义到北大去工作。到那里后,她首先去找北大党支部的负责人侯瑞。
侯瑞是个二十四岁的瘦瘦的青年,北大历史系四年级的学生。正好和王晓燕是同班。一个下午,道静作为他的同乡,拿着组织的介绍信,在北大灰楼二楼侯瑞的小单间房内和他见了面。见了面没有任何客套,他们关好屋门立即开始了简短的谈话。
“你来了很好。”侯瑞的两只眼睛相离很远,说话带着和蔼的笑容,“北大党的力量在最近两年连续遭到几次的逮捕、镇压之后,已经很微弱,到现在还没有恢复上来。”
“那么,你和徐辉怎么能够保存下去?你们一定有好的经验吧。”
侯瑞笑了。他看看窗外,回过头来悄悄说:“保护色保护得好呗。一般学生看起来,我是个拙笨的埋头读书的好学生,不看准了对象,我难得向他谈出自己的思想。徐辉比我更能干,有一阵子,她和那些落后的甚至反动的学生也来往一二,这就当然不为敌人注意喽。”
“但是……”道静本想说,你这样像蜗牛一样睡在壳里怎么开展工作呢?但她没说出来,却问起了王晓燕的情况。
侯瑞笑笑说:“北大的托派活动很有历史。原来名为‘动力’派的托派,后来和陶希圣的‘新生命’派合流。这些家伙们专以‘左’的面目来欺骗年轻幼稚的学生,也专干破坏同学团结的勾当。而且暗中和国民党C.C.的学生勾结在一起,侦察学生的行动,告个密,领个赏,还不是那么回事!”
说到这里,他好像才想起似的看着道静微笑道,“你不是要问王晓燕的情况么?她可变坏了。她就是和这些托派学生混在一起了。历史系三年级的学生王忠是我们学校的托派头子,近来他们很接近。”接着他把学生当中的情况,又向道静介绍了一些。
道静瞅着侯瑞那张瘦瘦的总是含笑的脸,半晌没说话。她在思考怎么办,她在为她朋友的遭遇痛心着。过了一会儿,好像要摆脱这沉重的负担,她突然从坐着的小椅子上站了起来说:“侯瑞同志,现在咱们谈谈北大的工作怎么样开展吧。根据区委的意见,有光荣传统的北大,可不该叫它像现在这样老大下去。看,北平各个大学随着华北形势的紧张都活跃起来了,可是,北大的学生会我们还不能掌握,这样,我们就没有力量来领导群众斗争。我看,咱们是不是首先要发动进步力量把学生会夺取过来呢?”
侯瑞笑笑说:“这个工作我们早就在进行。可是……北大受摧残太重了,一下不易……”
道静当时没有多说什么,她和侯瑞谈了要去找晓燕的意思就走了。
她决定开始进行她的工作。第一,去找晓燕。得机会揭露戴愉是个什么样的家伙,争取晓燕抛开他。第二,她要在北大安下身来、听课并参加一些群众活动。因为北京大学是一个有历史传统的“自由”学府,至少外表上学生听课、选课、出来进去都很随便。有些不是北大的学生可以坐在北大课堂上去听课,不但有些教授认不清,就是同学之间也常是互不认识。
道静刚搬到沙滩附近腊库胡同的一间小民房里,就急忙去找王晓燕。自从和刘大姐去住机关,她就没有再见过她。尽管她和戴愉的关系使道静懊恼,但是多年的友情和对于晓燕的信任,使她依然深切地关心她、想念她。当她踏上晓燕房间的台阶时,心里还在热切地期待着一场欢畅的叙谈和真挚的友情的慰藉。
但是事实大大出于她的意料之外,她一见王晓燕就深深被惊异与失望震动了。
晓燕正埋头在桌上写东西,一见道静走进屋来,好像见了什么妖怪似地陡然一惊,接着立刻满脸通红。她头也不抬,冷淡地好像对陌生人讲话一样:“来啦?有什么事吗?”
道静按捺住自己的惊讶和恼火,轻轻走到晓燕身边,拉住了她的手:“燕,你怎么啦?三个多月不见,真怪想你……”想不到晓燕把手一抽,把头一扭竟不理她。道静的脸都气白了,声音都发抖了:“你?王晓燕,我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地方?……”
晓燕坐在桌边仍又写起她的东西,并不搭腔。道静只得怔在她旁边,小屋里是一阵难耐的沉寂。
“不,一定要搞明白!”道静在心里下了决心。
“晓燕,你是不是听了什么人的挑拨了?为什么,为什么变得——变得这样?……”
晓燕慢慢抬起头来直视着道静。从那双悲伤的黑色的圆眼睛里,道静看出了它是怎样被痛苦和恐惧缠绕着。终于又从这双善良的圆眼睛里簌簌地滚下了大粒的泪珠——王晓燕坐在桌旁捂着脸哭了。
道静惊疑地看着她。这意外的遭遇,这问也问不出来的疑团使她走也不是,坐也不是。
“晓燕,难道你不认识我了?难道我……”道静的眼睛炯炯地盯着晓燕看着,她已经对一直一言不发的王晓燕提高了警惕,“晓燕,我走了。有什么意见以后再谈吧。我过去读书太少,现在打算在北大旁听课,我们会常碰面的。”
晓燕仍然一言不发。她抬起头看着道静,仿佛监视她是否会偷走东西似的。
两天后的下午,道静听过了两堂古代史的课,在红楼外面的马路旁迎面碰到了王晓燕。她似乎要躲避道静,但道静却迎着她走了过去。
“王晓燕,你上课去?”道静若无其事地笑着和她招呼,“王伯父近来情况怎么样?伯母和凌燕她们都好?”
晓燕似乎不好意思再不讲话了,冷冷地,然而仍掩饰不住她的痛苦,小声说:“谢谢!他们很好……你是来听课的吗?”
道静抓紧机会赶忙抓住晓燕的手:“晓燕,你一定有许多痛苦为难的事,但是我不勉强你回答我。”沉了沉她又说,“我听说你近来变了,我心里很难受……如果你还相信我,那你就该考虑一下……”她看了看周围,看了看晓燕的眼色,没有把话谈下去。
晓燕的眼神是恐惧的、惊疑不定的。她盯着道静张嘴想说什么,但是没等说出来,却逃跑似的急忙转身走掉。
这意外的遭遇——晓燕对她态度的突变,打乱了她的计划,造成了新的困难。这种变化,她估计到一定是受了戴愉的挑拨和欺骗。但是那个叛徒用什么办法和口实造成这样情况的呢,道静一时却还没有办法猜度出来。晓燕在学生中是有威信的,现在还在学生会中负有相当的责任,如不能把她教育争取过来,那么她将为敌人所利用。想到这儿,道静的心情非常沉重。深夜她在自己新租下的冷清的小屋中走来走去,不能入睡。
又过了两天,道静才从北大红楼二楼上听完课,随着一些学生走下楼来的时候,在楼梯的转角处,突然有两个男学生跳到她跟前。一个人抓住了她的双臂,另一个有着猴子样瘦脸的人,就左右开弓,狠狠地打起她的嘴巴来。打够了,挥着拳头骂道:“叛徒!奸细!无耻的女光棍!竟敢跑到堂堂北大来听课,滚出去!”
这一个刚住口,另一个又举起拳头骂起来:“再看见你冒充学生走进来,叫你屁滚尿流滚出去!”
道静愤怒地反抗着。她挣扎着,把手猛力伸向打她的猴子脸。但是这时又有四只粗暴的手,猛地猝不及防地把她从楼上像一堆碎石样推了下去。她摔下去,匍伏在楼梯上,滚着、挣扎着。当她踉跄地要站起身来,同时被另外两个学生扶了起来的一霎间,她发现站在楼上旁观的、像看把戏般的一群学生中间,站着面色苍白的王晓燕。而挨着晓燕身边笑着、和她谈说什么的就是那个打她的猴子脸。
道静感到一阵眩晕,感到比刚才有人打她嘴巴更难忍受的愤怒与痛楚。在这个新的地方有谁知道她林道静呢?只有她——她一生中最好的朋友王晓燕知道。那么,是被她出卖了?被这最好的朋友出卖了?这是多么可怕的想法呀!然而她却不能不这样想。因为晓燕明明站在她面前……她激怒地瞪着王晓燕,顺着嘴角涌流出来的鲜血涂了她一手掌。
当晚道静和北大的三个党员同志——侯瑞、吴禹平、刘丽开了一次紧急会议。他们开会的地点是在刘丽的家里。刘丽是外语系的学生,二十二岁。她长的矮小伶俐,看起来只有十七八岁。道静的被打,激起了同志们的愤怒,他们坐在刘丽的朴素洁净的房间里,会议开得紧张而迅速。
道静首先发言:“根据上级党的意见,和我对北大的一点了解,目前我们最主要的任务是要唤醒或者说是推动……”道静的两颊是红肿的,她不得不戴了一个大口罩。因为感觉说话不便,这时,她摘下口罩继续说道:“那些曾经积极参加过救亡活动、有一定认识的同学,要使他们振奋起来,以他们为骨干再去广泛团结中间的同学。我们党员太少了,如果不能把那些思想进步的同学发动起来,那么,我们就无法打破北大这种空前的沉寂状况。”
刘丽接着道静的话发言道:“路芳同志的话很对。我们不能做有名无实的党员,不能总在困难面前裹足不前。自从徐辉调走后的这一个时期,剩下我们几个人,因为怕暴露,怕再遭受逮捕,是太过于保守了。看看人家清华、燕京,”她忽然把手一挥,严肃地看了侯瑞一眼,“看清华、燕京的各种救亡活动多么活跃,没有问题,这是党员在那里起作用。是党的组织发挥了战斗性。我以为我们北大也应该是这样!”
她说话干脆、尖锐、有力量,和她那圆圆的好像孩子般的面孔有些不相称似的。
“事情不像你说的那么简单吧?”说话的吴禹平也只有二十二三岁,他的声音又慢又沉闷。他看看道静,又看看侯瑞,最后把眼光落在刘丽的脸上,“各个学校的情况不同,我看绝不能一概而论。去年北大的社联,又遭受了一次严重的破坏,元气大伤,现在广大同学虽然是有爱国热情,可是,马上推动他们行动起来,我看还有点为时过早……”
“什么过早?……”刘丽忍耐不住,几乎要喊出声来。侯瑞又用眼睛又用手势制止了她的激动,然后慢条斯理地笑道:“小刘,情况是很复杂嘛,你、你着急有什么用!一九三四年是全国最黑暗的年代,也是北平最黑暗的时期。这个时期光拿北大来说吧,什么C.C.、托派、国家主义派、无政府主义派……全蜂拥而出,一齐登上了政治舞台。我们要赶走他们,那是一定的,可、可是……”
“可是什么?”道静紧盯着侯瑞的嘴巴,她不由得也插了一句。
侯瑞仍然不慌不忙地笑道:“可是太着急了,并没有用。党剩下的力量不大了,我们要珍惜这点力量,因为这是革命的本钱。”
还没容道静张嘴,刘丽又挥挥手——好像有什么东西在阻拦她讲话,而她要赶走这些东西似的——极力压低了声音说:“老侯,要照你这么说,咱们永远躺在安乐椅上不要动弹啦。我忍耐又忍耐,我看许多同学也是忍耐又忍耐,可是,你还叫我们忍耐到什么时候呢?什么时候反革命会自动退出政治舞台呢?”
侯瑞瘦瘦的黄脸有点儿涨红了,他又环顾了道静和吴禹平一下,结结巴巴地说:“小刘,别、别这么说。难道我、我是不、不想革命吗?不,我是坚决地……我只是怕我们的力量再、再受挫折……”
“挫折!挫折!又是你那个挫折!”刘丽抢着说完这句话,好像要哭似的用双手蒙起了眼睛。
把这些都看到眼里的道静,心头突然像堵上了一块铅板——又沉重、又不安。她虽然觉得侯瑞和吴禹平的见解、做法都有问题,但是她是刚刚派来帮助工作的,而且对情况并不甚了解,当她觉得一时还没有力量把这一切都澄清、扭转的时候,她就更加恼恨起自己来:“究竟怎样才好呢?……”
她看着北大的三个同志,自己问起自己来。
四个人都闷闷地低头沉思了一下,还是道静先张嘴问侯瑞:“那依你说,咱们北大的工作该怎样进行才是?”
侯瑞还是不慌不忙地笑了笑:“目前,北平正在酝酿成立统一的学联,北大的学生组织还七零八落,我看我们可以分头活动,慢慢把这个摊子收拾起来。”
“不是慢慢,而是快快!”刘丽像炒爆豆似的小嘴,又向侯瑞攻了一炮,“我们要赶快分头发动同学起来斗争,而不是慢慢地等着挨打!”
“对,应当快一点。”道静也加了一句,“我想,北大如果要想参加学联,那首先就必须把进步力量组织起来,然后尽量争取中间分子,孤立那些反动家伙……”
“这个嘛,理所当然的道理!”许久没有发言的吴禹平,文诌诌地细声细气地给了道静一句。道静觉得很不是滋味,但她顾不得多想什么,也不愿多想下去,只是极力克制自己的感情,而且鼓起极大的勇气看了吴禹平一眼,轻轻地说完她要说的话:“当然,我所说的只是一般的原则。只是根据党中央目前抗日政策的精神来说。至于怎样具体执行,那,我不如你们了解情况,也没有你们经验多。反正团结进步、争取中间、孤立反动,这个方针我们应当是确定不移地去执行。”
吴禹平低头摆弄着手里的钢笔没有搭腔;刘丽睁着亮亮的眸子目不转睛地看着道静红肿的脸颊,也没有说话;侯瑞笑笑说道:“好吧,咱们就布置团员和积极分子活动起来吧。北大当然要想办法改选学生会争取参加学联。”说到这里,他像刚想起来似的问道静,“路芳,王晓燕的问题,你以后打算怎么办?”
“理她干什么!”爽直的刘丽又脱口而出。
侯瑞眯着眼睛看着刘丽摇摇头:“依着你这个炮仗脾气早把工作都弄糟了。王晓燕是不自觉的上了托派的当,我看还是可以争取她的。”
道静沉思着说:“她还能算中间分子?我现在倒是同意刘丽的意见,咱们不要理她了。”
“理这样的人干么?”吴禹平也加了一句。
侯瑞摇摇头说:“我和她同班,比较了解她的情况。虽然因为她,反动家伙们打了你……”说到这里,侯瑞不自觉地瞟了道静一眼——那红肿的、有着斑驳血印的两颊,这时忽然这样清晰地映入到他的眼里,使他的心不禁翻搅了一下。
“假如,我们的力量是强大的,假如我们的工作做得好,她,她怎么会挨打呢?她刚刚来,我们的同志……”侯瑞的这种痛苦心情,连刘丽、吴禹平也立刻感染上了。他们也同时负疚似的看了道静一眼。但是看到她沉思的、似乎丝毫没有想到挨打这件事的神情,这三个同志更加不安起来了。小屋里顿时沉寂下来。
“王晓燕是个固执、自信、不大容易说话的人。”侯瑞看大家全不讲话,就接着说道,“不过倒是个老实的好人,我看只有用事实来揭破了托派的欺骗、虚伪,才能使她惊醒过来。”
“侯瑞的话很对。”道静说,“我很了解她的个性,确是这样。不过,我已经不能再和她接近。如果说到中间分子么,我看,我去接近李槐英还比较合适。”
“我看不必吧。”侯瑞和吴禹平几乎是同时说出这句话,“这位花王小姐,怎能是我们驾驭得了的。”
“不,我们过去认识,我愿意试试看。”道静坚持说。这个会就这样散了。几个同志站起身来要走的时候,道静又戴上了她那个大口罩。这时刘丽站在角落里看着她,等两个男同志先走出去了,她一下扑到道静身边,用柔软的小手紧紧拉住她的手,说:“疼吧?要不要紧?要不,在我家里休息两天,我爸爸妈妈全很好的。”
感到了同志间诚挚的关切,白天挨打、受辱时没流一滴眼泪的道静,这时反倒热泪盈眶了。对这第一次才见面的陌生的同志,她好像对自己最亲近的人一般,吐露出内心里的话语:“刘丽,没有什么。疼倒不觉得,只是我们的工作……”
说到这里,她有些不好意思似的紧紧握住了刘丽的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