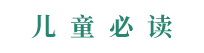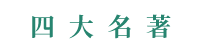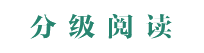断续经过六年,把这书写成之后,我确有如释重负的轻快之感。我想,许多人都会有过这样的感觉:有什么能比完成了一件人民交给自己的艰巨任务更快乐的呢?说实在的,对我这样一个虽不年轻、但对文学还是个初学写作者来说,写这样一部长篇确是很吃力的。我的斗争经验和艺术表现能力既很浅薄,而且身体又长年处在病痛中,精神时时有不支之感。可是,我为什么竟不自量力地写下来呢?是什么力量支持我前后做了六七次的重写、修改,熬过了漫长的时日呢?提起这个,我的心中仍然不免激动……我要真诚地告诉读者们:我的整个幼年和青年的一段时间,曾经生活在国民党统治下的黑暗社会中,受尽了压榨、迫害和失学失业的痛苦,那生活深深烙印在我的心中,使我时常有要控诉的愿望;而在那暗无天日的日子中,正当我走投无路的时候,幸而遇见了党。是党拯救了我,使我在绝望中看见了光明,看见了人类的美丽的远景;是党给了我一个真正的生命,使我有勇气和力量度过了长期的残酷的战争岁月,而终于成为革命队伍中的一员……这感激,这刻骨的感念,就成为这部小说的原始的基础。
一九三三年前后,在残酷的白区地下斗争中,我直接接触的和间接听到的共产党员和革命青年的英勇斗争、宁死不屈的事迹,是怎样的使人感动呵!是怎样的使人想跟他们学习、想更好地生活呵!这些人长期活在我的心中,使我多年来渴望有机会能够表现他们。所以这书中的许多人和事基本上都是真实的,譬如书中篇幅不多的林红就真有其人。这个异常美丽的女同志是英勇地牺牲在山东军阀韩复榘的屠刀下的。就是这些人鼓舞我写,就是这些人给了我力量。一想到这些人,懒惰、胆怯的手就勤奋起来,勇气也就大起来了。
我终于敢写的原因,是我喜欢文学,也愿意用这个武器做一点对人民有益的事。可是我自知水平很差,因此对那些澎湃复杂的斗争,对那些光辉灿烂的人物,对敌人的阴毒凶狠,我还难于表现它们于万一;如果这部小说真能让青年同志们看看过去的人们是怎样生活、斗争过来的,也许他们对今天的新社会、今天的幸福生活就会更珍爱一些,——而这也就是我对这本书的最高愿望了。
一九五七年九月于北京
再版后记
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大跃进的形势鼓舞下,我用了三个月的时间,把《青春之歌》修改出来了。修改本和初版本比较,有许多地方不同。改得究竟如何,我自己还不敢肯定,还有待广大读者的检验。但是,在主观上我曾经极力改正初版本中所发现的缺点或错误,并设法弥补某些不足之处。其中变动最大的,是增加了林道静在农村的七和北大学生运动的三。而这些变动的基本意图是围绕林道静这个主要人物,要使她的成长更加合情合理、脉络清楚,要使她从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变成无产阶级战士的发展过程更加令人信服,更有坚实的基础。同时也对其他人物或情节作了某些必要的修改。
这样做是不是必要呢?我认为是必要的。我常想,作者和作品的关系可以比作母亲和孩子的关系。母亲不但要孕育、生养自己的孩子,而且还要把他教育成人,让他能够为人民为祖国有所贡献,做一个有用之材。假如发现自己的孩子有了毛病、缺点,做母亲的首先要严格地纠正他,要帮他走上正确的道路。即使孩子已经是社会上的人了,已经起过一些作用了,做母亲的也还应该关心他、帮助他克服缺点,尽自己的一切力量使得他变成一个更加完美的人。就在这种心情支使下,我就尽我微薄的力量又把《青春之歌》修改了一遍。
不过因为时间的仓促,因为生活经验的不足,更因为自己政治水平不够高,这部小说可能还存在许多缺点。
提到修改小说,不能不提到今年《中国青年》和《文艺报》对《青春之歌》初版本所展开的讨论。这种讨论对我来说是非常有益的。俗语常说:“文章是自己的‘好’。”因为作者对自己写出的作品常常不易看出其中的症结和毛病。这就需要批评家,尤其是广大读者的帮助。我这次修改《青春之歌》,基本上就是吸收了这次讨论中的各种中肯的、可行的意见。这种讨论不仅使我对艺术创作上的一些问题比较清楚了,而且使我的思想认识得到不少提高。说到这里,我深深感到文艺创作需要群众的监督、支持与帮助。也同时感到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关心孩子的不仅是他生身的母亲,而且还有千千万万不相识的人们。
《中国青年》和《文艺报》上的讨论,以及其他读者所提出的许多意见,集中起来可以分做这样几个主要方面:一、林道静的小资产阶级感情问题;二、林道静和工农结合问题;三、林道静入党后的作用问题——也就是“一二九”学生运动展示得不够宏阔有力的问题。这些问题在这次的修改本中我是这样把它们逐条解决的:首先,关于林道静的感情问题。林道静原是一个充满小资产阶级感情的知识分子,没参加革命前,或者没有经过严峻的思想改造前,叫她没有这种感情的流露,那是不真实的;但是在她接受了革命的教育以后,尤其在她参加了一段农村阶级斗争的革命风暴以后,在她经过监狱中更多的革命教育和锻炼以后,再过多地流露那种小资产阶级追怀往事的情感,那便会损伤这个人物,那便又会变成不真实的了。所以小说的后半部在这些方面有了不少的变动。说来,也怪有意思,林道静从农村受到锻炼回到北平后,我在修改本中原来对她的小资产阶级感情仍然改动得不太多,可是当我校看校样的时候,看到她在小说的后面还流露出不少不够健康的感情,便觉得非常不顺眼,觉得不能容忍,便又把这些地方做了修改。
从这里看,小说中的人物已经变成客观存在的东西,它的发展有它自己的规律。作者如果不洞悉这种规律,不掌握这种规律来创造人物,那就会歪曲人物,就会写出不真实的东西来。
其次,关于和工农结合问题。在“一二九”运动前,知识分子和工农结合虽然还没有充分的条件,但是既然已经写了林道静到了农村,既然党在那时的华北农村又有不小的力量,并且不断地领导农民向豪绅地主进行着各种斗争,那么,为什么不可以把林道静放到这种革命洪流中去锻炼一下呢?
为什么不可以通过我们的女主人公的活动去展示一下当时中国农村的面貌,并突破一下知识分子的圈子,叫读者的视野看到当时农民生活的悲惨,看到地主阶级的罪恶,从而激起更高的革命激情呢?这样一想,于是我就增写了林道静在农村的七。这还说不上是她和工农的结合,但是,我觉得给她这种锻炼和考验的机会,还是有用的。这个人物经过这些生活与斗争之后,她的面貌就不同了,作者想不提高她也不行了。
第三,经过同志们的指出,我确实也感到林道静在入党以后停滞了,发挥的作用不大。“一二九”也写得很不充分,全书实在有些虎头蛇尾。所以在这次的修改本里,我力图使入党后的林道静更成熟些,更坚强些,更有作为些。通过她,也把“一二九”学生运动的面貌尽可能写得充实些(因为生活的限制,我自己并没有参加过“一二九”,所以写来写去,怎么也无法写得更丰满。)
总之,修改都是围绕着林道静的成长,围绕着林道静所走的道路,围绕林道静这个人物的典型意义来进行的。
当然,除此以外,零零碎碎也还有不少改动的地方。比如戴愉这个人物我就改做由特务头子把他弄死,而不由我们处死他了。因为这样更合乎当时的实际情况。
初版问世的将近两年中,我接到了不少读者来信。他们关心书中的人物,希望知道林道静是否实有其人。我愿意在这里捎带谈一谈。林道静是真的又是假的。为什么这样说呢?
如果作为“九一八”至“一二九”这个阶段,知识分子在党领导下走向革命的典型人物来说,作为艺术的真实来说,她是真的。因为当时千千万万的青年知识分子(尤其是女同志)都和她有着大致相同的生活遭遇,大致相同的思想、感情,大致相同地从寻找个人出路而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所以我说她是真的。为什么又说她是假的呢?因为确确实实世界上不曾有过林道静这样一个人。她是由几个或者更多的人的影子糅合在一起而创造出来的。初版后记中,我曾说过“这书中的许多人和事基本上都是真实的”,为什么说基本上真实而不说完全真实呢?这就受文艺创作的规律所决定。它必须用概括、集中的手法,把许多同类型的人的生活事迹集中到一起,创造出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
谈到小说中的其他人物,大体上也和林道静的情形差不多。有的人有个“模特儿”,再加上其他同类型人的生活凑在一起,就变成了小说里的人物;有的连“模特儿”都没有,完全是我想象出来的。比方卢嘉川就是这样情形。他虽然是虚构的,但却是我二十多年来在斗争生活中对于共产党员的观察、体会所凝聚出来的真实人物。这个崇高的共产党员的形象绝不虚假。他是从生活当中提炼出来的最真实的形象。在全书中我爱他和爱林红超过于任何人。在这次修改本中我对于这两个人物几乎没有什么改动。
创作,这是一门很有意思的劳动。作家创造出来的形象不仅可以教育和感动读者,同样也可以教育和感动作者本人。
在创造卢嘉川、林红这些视死如归的共产党员形象的过程中,我自己的精神世界就仿佛升华了,就仿佛飞扬到崇高的境界中。他们今天已经成了我心目中活的导师和朋友。因为这样,我才感到很难把他们的形象再加改动。
国庆十周年前夕,我漫步在首都天安门前。夜间,灯火齐明,照出一座座新建的高大建筑物,宛如一座座眩人眼目的水晶宫殿。美丽的灯光,狂欢的人群,祖国十年来的伟大成就,不禁使我回忆到过去——回忆到“七七事变”前我在北京生活时的那些情景。同是一个天安门和玉带河,可是那时候,在这里逗留的不是今天这些沉醉在胜利的狂歌欢舞中的青年;也不是列成整齐雄健的队伍,带着欢乐而自豪的心情,通过天安门前接受毛主席检阅的青年。那时,聚集到这里来的却是那些怀着沉痛的心情,带着满身的尘土甚至带着斑斑的血迹,声嘶力竭地呼喊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人起来救中国!”的青年人。那时,徘徊在这里的人们,眼看着雄伟的天安门油漆剥落,仿佛沉睡在厚厚的灰尘中,谁的心情不感到沉重?谁的眼睛里不是满目凄凉?……可是这种情景,今天的青年同志再也不能看到——永远也无法看到了!要想看,只能从历史、文物,尤其从文艺作品中去找寻。
可是,《青春之歌》在这方面远没有尽到它的职责——这是我在国庆前夕,从天安门前的辉煌情景中,才感觉出来的。不过已经来不及补救了。现在,我就把当年天安门前的情景在后记中补上几句,聊以作为我向青年同志们的负疚的一点表示吧。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于北京
《青春之歌》的最初问世是在一九五八年一月,迄今已三十三年了。当一九九一年六月,它将在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重版出书时,我不禁感慨万千。它刚刚问世时,我才四十岁出头,还算是风华正茂,而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我已垂垂老矣。几十年岁月,人事沧桑,世事更迭,亦喜亦忧,良多感叹。只是我对《青春之歌》的看法与情感却从未变更,从未迁移。因为它是我投身革命的印痕,是我生命中最灿烂时刻的闪光。它如果泯灭,便是我理想的泯灭,生命的泯灭。它的命运就是我的命运……
《青春之歌》刚一出世虽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喜爱,但鞭挞、批判却很快地汹涌而来。有名的自称是“工人代表”的那位郭先生首先向它发难,说它是歌颂美化了小资产阶级,说主人公林道静不配是个共产党员……一时间,《中国青年》、《文艺报》等报刊展开了热烈地论争。我不知道我国当代文学作品中(也许除了《武训传》?)还有哪一部曾受到如此广泛、如此连篇累牍地批判(当然也有大量反批判的拥护者)。从一九五八年底开始,对《青春之歌》的批判、讨论持续了三个多月。有无限上纲的,有据理力争的,声势浩大,黑云压顶。我气馁、消沉了么?没有!我沉稳地静观事态的发展。因为我心中有底——笃信鲁迅的名言;“从喷泉中流出的是水,从血管里流出的是血。”我自认为《青春之歌》是我血泪凝聚的晶石,它不会贻害人民。果然,最后由茅盾、何其芳、马铁丁几位先生写了结论式的长篇文章,《青春之歌》才站住了,才继续大量发行。
平安了几年,“文革”时期,《青春之歌》的厄运又来了!
还是那位郭先生,又起来发难。这次《青春之歌》的罪名是“为刘少奇、彭真树碑立传”的特大毒草;接着全国有二百多种小报,有无数次的批判会,对它“口诛笔伐”。它成了“文革”中受批判最重的“大毒草”之一。彼时我人身不大自由了,但我的心还是自由的。我不知世事将如何发展,我不知《青春之歌》的命运如何,但我的内心依然爱它、信它,依然坚信血就是血,不是水。
果然,一九七七年,“文革”结束不久,《青春之歌》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又重新出版了。它又经历了一次磨难,一次浩劫。
我对它的感觉不是复苏,不是再生,而是一株小树经受风雨后又吐出嫩芽的欣欣向荣的喜悦。我不能忘记前两年有一位大学生给我写信说,他是在原中学校大批焚毁“毒草”书时,冒着危险,偷偷从大火中抢救出了一本《青春之歌》而读到它的;优秀青年张海迪姑娘,当着魏巍同志的面亲口对我说,她也是在“文革”中连夜偷看残本的《青春之歌》的。他们读后都受到鼓舞,都非常爱它。一本书能得到不同年代的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的挚爱,这对于一个作者来说尽够了,尽够了……
我深知它今后仍然不会一帆风顺,仍然会遭到某些非议。
不是么,一位澳大利亚的来我国学习的留学生,去年写信给我说,他的老师就曾批评《青春之歌》不该增加农村斗争那几章(不少人都有此看法),问我对此有什么意见。还有的青年作家,说《青春之歌》是个“表达既定概念的作品”。还有的人说,这小说不过是“爱情加革命”的图解云云。他们的看法都各有道理。我呢,也有我的道理。我推崇现实主义创作法则,我的生活经历,我的信仰决定了我的爱与憎,也决定了我喜欢写什么,不喜欢写什么。这无法更改。我不想媚俗,不想邀某些读者之宠;我只能以一颗忠诚于祖国、人民,热爱共产主义的心来从事我的创作。我希望我的作品能有助于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了解旧中国危殆的过去,向往新中国光明的未来。这也许又是老生常谈。但该常谈的总不免要常谈。这只有请读者原谅了。
一九九一年六月八日晨于香山东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