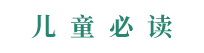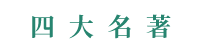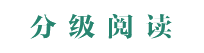在我们这个星球上,每天都要发生许多变化,有人倒霉了,有人走运了,有人在创造历史,历史也在成全或抛弃某些人。每一分钟都有新的生命欣喜地降生到这个世界,同时也把另一些人送进坟墓。这边万里无云,阳光灿烂;那边就可能风云骤起,地裂山崩。世界没有一天是平静的。可是对大多数人来说,生活的变化是缓慢的。今天和昨天似乎没有什么不同,明天也可能和今天一样。也许人一生仅仅有那么一两个辉煌的瞬间——甚至一生都可能在平淡无奇中度过。不过,细想过来,每个人的生活同样也是一个世界。即是最平凡的人,也得要为他那个世界的存在而战斗。从这个意义上说,在这些平凡的世界里,也没有一天是平静的。因此,大多数普通人不会像飘飘欲仙的老庄,时常把自己看作是一粒尘埃——尽管地球在浩渺的宇宙中也只不过是一粒尘埃罢了。幸亏人们没有都去信奉“庄子主义”,否则这世界就会到处充斥着这些看破红尘而又自命不凡的家伙。普通人时刻都为具体的生活而伤神费力——尽管在某些超凡脱俗的雅士看来,这些芸芸众生的努力是那么不值一提。
孙少平已经适应了这个底层社会的生活。尽管他有香皂和牙具,也不往出拿。不洗脸,不洗脚,更不要说刷牙了。吃饭和别人一样,端着老碗往地上一蹲,有声有响地往嘴里扒拉。说话是粗鲁的。走路拱着腰,手背抄起或筒在袖口里,两条腿故意弄成罗圈形。吐痰像子弹出膛一般。大便完和其他工匠一样拿土坷垃当手纸。没有人看出他是个识字人,并且还当过“先生”呢。
虽然少平看起来成了一个地道的、外出谋生的庄稼人,但有一点他却没能做到,就是在晚上睡觉时常常失眠——这是文化人典型的毛病。好在别人一躺下就拉起了呼噜,谁知道他在黑暗中大睁着眼睛呢?如果大伙知道有一个人晚上睡不着觉,就像对一个不吃肥肉的人一样会感到不可思议。是的,劳筋损骨熬苦一天以后,孙少平也常常难以入眠,而且在静静的夜晚,一躺进黑暗中,他的思绪反而更活跃了。有时候他也想一些具体的事,但大多数情况下思想是漫无边际的,像没有河床的洪水在泛滥,又像五光十色的光环交叉重迭在一起——这些散乱的思绪一直要带进他的梦中。当然,不踏实的睡眠并不影响他第二天的劳动。他终究年轻,体力像拉圆的弓弦那般饱满。
转眼间,一个月过去了。清明之前,天气转暖,大地差不多完全解冻。黄原河岸边的柳枝,已经萌生起招惹人的绿意。周围山野里向阳的坡坂上,青草的嫩芽顶破潮润的地皮,准备出头露面在工艺厂的工地上。干活的人已经穿不住棉衣,一上工便脱下撂在了一边。现在,宿舍楼起了第一层,楼板安好后,开始砌第二层的屋墙。少平的工作是把浇过水的湿砖用手一块块往二层上扔——这需要多么大的臂力和耐力啊!这无疑是小工行里最苦的活,可是他应该干这活,因为他拿的是这一行的“高工资”。
这工地站场监工的是包工头胡永州的一个侄子,他年龄不大,倒跟上他叔叔学得有模有样,嘴里叼根黑棒卷烟,四处转悠着,从早到晚不离工地,指手划脚,吆吆喝喝。胡永州本人一般每天只来转一转,就不见了踪影——他同时包好几个工程,要四下里跑着指挥。晚上他是回这里来住的。胡永州和他侄子分别住在工地旁厂方腾出来的闲窑里。紧挨着的是灶房。做饭的除过那个雇来的小女孩,还有一位六十多岁的老汉,也是胡永州的亲戚,这老汉和胡永州的侄子住在了一孔窑里,那个小女孩晚上就单独在灶房里睡觉。其他工匠在这里吃完晚饭,就回到坡下那个垃圾堆旁的窑洞里去了。
孙少平搬到没门窗的楼房后,才想起这里晚上没灯。他就在外出采购东西的时候,捎带着给自己买了一些蜡烛。条件一具备,他就打算到晓霞那里去借几本书回来。
过罢清明节,少平在一个星期六的傍晚,破例拿出牙具和香皂,偷偷到小南河里洗刷了一番,又换上自己的那身“礼服”,就满有精神地去地委找田晓霞。在地委田福军的办公室和晓霞相会后,她又高兴又抱怨地问他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不来找她。少平吞吞吐吐解释了半天。一段时间没见晓霞,少平吃惊地发现她的个码似乎蹿高了一大截——他一时粗心,没有留意她换了一双高跟鞋。两个人像往常那样,一块吃了晓霞从大灶上买回来的饭菜,接着热烈地议论了许多话题。临走时,晓霞给他找了一本艾特玛托夫的《白轮船》。她告诉他,这是她很喜欢的一本书,是前几年内部发行的,父亲买回来后,她看完就偷偷地占为己有了。少平打开书,见书前有“任犊”写的一篇批判性序言。晓霞说,那“畜生”全是胡说八道,不值得理睬。少平很快和晓霞告辞了——既然这本书他的“导师”如此推崇,他就迫不及待地想读它。回到“新居”以后他点亮蜡烛,就躺在墙角麦秸草上的那一堆破被褥里,马上开始读这本小说。周围一片寂静,人们都已经沉沉地入睡了。带着凉意的晚风从洞开的窗户中吹进来,摇曳着豆粒般的烛光。
星期六好不容易到了。这天下午他耐到收工,就匆匆地拿了那本《白轮船》,到地委去找她。他见到晓霞后,一时倒不想说什么了。他本来急切地想和她谈论看过的书,但他又感到自己很难说清楚。这本书更多的是引起他情绪上的大波动——一个人是很难把自己的情绪说明白的。真的,这是一种无法用语言概述的感受,因为它太巨大太复杂了!田晓霞看出了这本书给孙少平带来的震动,她自己也曾被它强烈地感染过。她高兴的是,少平和她一样理解并喜欢这本书。
吃完下午饭,晓霞突然提议他们一块去爬一次麻雀山。这正合少平的心意。于是,两个人一同相跟着出了地委大门,向麻雀山走去。走在路上的时候,少平才有点拘束起来。和晓霞一块呆在房子里说话,他觉得很自然,可是,两个人一块相跟到野外去遛达,他就感到情调有点太温馨——不过,这种温馨是任何一个青年男子都不会反感的!麻雀山就在地委的后面。他们顺着一道缓坡慢慢向山上走。快到山顶时,晓霞顽皮地离开路径,专意在一些荒地里行走。少平就愉快地迁就她的任性,紧撵着她在没有路的地方向上攀行。一道土塄坎挡住了去路。少平敏捷地一扑就跳上去了。晓霞立在塄坎下,笑着摇了摇头,然后向他伸出一只手,要让他拉她。少平顿时有点慌乱,脸红得像水萝卜一样。晓霞被他的窘态逗得大笑,手却固执地伸着,非让他拉不行。少平只好伸出一只颤抖的手,把她拉上了土塄坎。这是他第一次拉一个姑娘的手。他感到自己的那条胳膊僵硬得像条棍子,手掌如同被烧红的铁烫过一般。山顶了。两个人在一个斜坡上坐下来。
两个人先顾不上说话,惊奇而兴奋地观赏夕阳晚照中的大自然景象。城市渐渐沉浸在阴暗中,景物开始模糊起来。黄原河上新老两座大桥首先亮起了灯火,紧接着,全城的灯火一批跟着一批亮了。这时候,晓霞才转过脸,问少平看过《白轮船》后,有什么感想。少平断断续续,结结巴巴说了一些,好像也没能把自己的感受充分表达出来。说实话吧,这会儿他思想不能集中起来!是呀,黄昏中,在一个荒山野地里,单独和一个姑娘呆在一块,使他浑身的血液由不得沸沸扬扬……内心的骚动让他坐立不安,他索性仰面躺在一片枯草上,两只手垫在脑后,茫然地望着暮色中的天空。天空已经亮出几颗星星。晓霞也就不再出声,静静地坐在离他不远的地方,两只手抱着膝头,凝望着远方的山峦。
这是一个美妙的时光。小树林中,归巢的鸟雀扇动着扑棱棱的羽翅。没有风,空气中流布着微微的温暖。春天的黄昏呀,使人产生无尽的遐思和深远的联想,也常常叫人感到一种无以名状的忧伤!躺在地上的孙少平,不知为什么突然眼里涌满了泪水。他深深地向夜空中吐出一声叹息,嘴里竟然喃喃地念起了《白轮船》中吉尔吉斯人的那首古歌——
有没有比你更宽阔的河流,爱耐塞,有没有比你更亲切的土地,爱耐塞,有没有比你更深重的苦难,爱耐塞,有没有比你更自由的意志,爱耐塞……
晓霞仍然保持着她那雕像似地凝望远山的姿势,接着他轻轻地念道——
少平猛一下从地上坐起来。一种强烈的冲动,使他真想伸开双臂,把田晓霞紧紧地抱住!山下的大街上传来一声刺耳的汽车喇叭的鸣叫。孙少平叹了一口气,抬起软绵绵的胳膊,用手掌揩掉额头的一层冷汗,对田晓霞说:“咱们回去吧。”晓霞没有说话,对他点点头。两个人就沉默地起身下山。山下,繁密灿烂的灯火,组成了一个无比辉煌的世界。孙少平在南关的大街上和田晓霞分了手,胳膊窝里夹着一本新借来的《简·爱》,就回他那个门户洞开的住处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