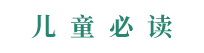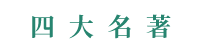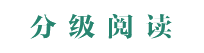这是五月里一个温暖的傍晚,田晓霞从宿舍里走出来,一个人在校园的路径上慢慢遛达着。路两边笔直的白杨树已经缀满了嫩绿的叶片。晚风和树叶在谈心,发出一些人所不能理解的细微声响。
田晓霞忍不住立在路边,面对着梧桐山那面升起的一轮明月发了会呆。她望着幽深的蓝天,吸吮着深春的气息,心里火辣辣的。她突然发现自己未免有点“小布尔乔亚”了,便由不得哈哈一笑,稍微加快点脚步,向前面走去。
在刚踏入黄原师专的时候,有一件事就在田晓霞的内心深处搅动起来:师专毕业后,她去干什么?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这所学校是师范性质的,培养学生的目标,就是毕业后在黄原几个地区去当中学教师。这是她很不愿意从事的职业。一生当个教书匠,这对她来说是难以想象的。尽管她在理性上承认这是一个崇高的职业,但绝对不合她的心意。她天性中有一种闯荡和冒险精神,希望自己的一生充满火热的情调,哪怕去西藏或新疆去当一名地质队员呢!但要摆脱当教师的命运,又绝非易事。这学校的历届毕业生,很少有过例外。首先必须去当教师,然后才可能从教师队伍中转向另外工作——这也是少数有能耐的人才可以做到的。当然,她父亲是地委书记,可以走点“后门”,把她分配到行政单位。但她对行政工作比当教师更反感。再说,她父亲也不一定会给她走这个后门。她有时很为这件事苦恼;甚至都有点精神不振和自制力松懈,以至影响了学习和进取心。
但她也能较快地从这种状态中解脱出来。每当她面临精神危机的时候,紧跟着便会对自己进行一番严厉的内心反省。她意识到,虽然随着年龄和知识的增长,她成熟了许多,但也不可避免地沾染上某些属于市民的意识。虽然她一直是鄙薄这些东西的,可又难免“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也许人为了生存,有时也不得不采取一些。但这些东西像是腐蚀剂,必然带来眼界狭窄、自制力减弱、奋斗精神衰退等等弊病。田晓霞毕竟是田晓霞!即使有时候主观上觉得倒退是可以的,但客观上却是无法忍受的,她必须永远是一个生活的强者!
经过内心的反复折腾后,晓霞迫使自己不要过分为这事而伤脑筋。车到山前必有路——到时再说吧,反正现在苦恼也无济于事。当然,她不是把这件事完全抛在了脑后,只是先作“淡化”处理。但最近以来,另一件事又在她心里七上八下地搅动——这是由于孙少平的出现而引起的。她在上高中时,就和孙少平的关系非同一般。不过那时他们的交往的确很单纯。她和这个同村而不熟悉的乡下学生初次相识,他身上的许多东西就引起了她的重视或者说另眼相看。后来,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加深了。但她和他在黄原相见之前,这种关系仅仅在同学之外另多了一种友谊的成份。在他们的年龄,这种关系是正常的,只是稍稍有些不平常罢了。
自从她在东关电影院门口碰见到黄原谋生的孙少平以来,在近一年的时间里,她对这个人的心情产生了某些微妙的变化。她现在总是在想着他。她常有点心神不安地等待星期六的到来,期望在父亲的办公室里,和他一块吃顿饭,天上地下谈论一番。她发现,班上现在还没有一个男生能代替少平和她在广阔的范围内交流思想。仅仅是为了交流思想,她才如此渴望和他在一块吗?不,这个人在很大程度上已经牵动了她内心中那根感情的弦索。是爱情?但她又觉得一切还没那么明确。她笼统地认为,对她来说,爱情大概还是一件相当遥远的事。她在学习上的进取心和对未来事业的抱负,在很大程度上占据了她的心,使她对个人问题的考虑缺乏一种强烈追求的意识。可是,她又为什么一想起他,心头就会泛起一层温热的波澜?她又为什么常常渴望和他呆在一块?甚至多时不见面一种想念之情就会油然而生。是爱情?也许这就是爱情!只不过她自己还没有明确承认罢了。
这样想的时候,我们的“小伙子”田晓霞也会臊得满脸飞霞。噢,不!最好先不要匆忙地说这种事。一种真正美好的感情,像酒一样,在坛子里藏得越长,味道也许更醇美。另外,从谈恋爱的意义上衡量,她和少平目前还有一种难以说清的距离感。先就保持这种关系吧!这已经使她的内心够乱了,她还要集中精力把大学上完呢!但不论怎样,她和少平每个星期六的相见,总使她的心情久久难以平静下来。前天晚上,他们又一块谈了那么多!并且再一次登上麻雀山,在月光下坐了好长时间。她知道,他现在又到地区柴油机厂给人家修建家属楼。他每星期在她手里拿走一本书,下个星期再换一本,他说他一个人住在正修建的楼房里,为的是晚上能安安静静看书。她无法想象,他在没门没窗、也没电灯的房间里怎样读这些书的!有几次她按捺不住自己的冲动,想晚上去找他,看他究竟住在一个什么样的地方。但她又打消了这念头。她要顾及他的自尊心——他不会愿意让她目睹他的处境。
田晓霞在温暖的晚风中走过校园内那条长长的林荫道。前面不远处就是图书馆——她正是到那里去的。晚饭后宿舍里同伴们叽叽喳喳,互相打闹个没完,她感到心烦,就想到图书馆的阅览室翻翻新出的杂志。晓霞进入灯火通明的阅览室后,却意外地看见了中学时的同学顾养民也在这里。养民也发现了她,手里拿一本翻开的大型文学期刊,热情地走过来和她握手。“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她问顾养民。养民的父亲顾尔纯副教授是师专的副校长,还给他们班讲授唐宋文学课。“我爷爷病了,我回原西看了一下,今天下午才返回到这里。我父母亲现在又回去了。我准备过一两天就回学校去。”风度翩翩的顾养民说着,就招呼她在一个长条木栏椅上一块坐下来。
“你也看文学杂志?”晓霞指了指他手中的那本期刊。“平时功课压得很重。没时间看。这几天没事,随便翻翻小说。现在文学创作很活跃,我们接触的不多。”顾养民谈吐自然,给人一种很成熟的印象。他瘦高个,脸色有点苍白,近视镜的度数看来不浅。他和晓霞很快谈论起了中学时的生活,他向她打问原来一些同学目前的情况——但没有提起过郝红梅。因为不是一个班,晓霞实际上也并不清楚他和红梅的关系。其他人的情况晓霞一无所知,她只是给他简单说了一下孙少平的情况——这是顾养民第一个就问到的人。另外,她还告诉他,听少平说,金波也在黄原东关的邮政所当临时工。至于她哥田润生,养民压根没提起过,她也几乎把他忘了。在他们的印象中,像田润生这样没什么特点的同学,根本不值得一提。
顾养民显得很兴奋,他说:“老同学们遇一回也不容易,你能不能把少平和金波找来,咱们一块在我家里吃一点饭,好好拉拉话,正好我父母亲也不在,家里很清静。”晓霞也觉得这个聚会很有意思,就答应说她明天就去找孙少平。
第二天下午没有课,晓霞就骑了个自行车,破例到城南柴油机厂的工地上去找孙少平。她以前很少来这里,一路打问着,才好不容易在一条小沟岔上找到了柴油机厂。进了柴油机厂,她又打听着找到建筑工地上来了。
孙少平站在脚手架上,往正在砌房墙的三层楼上扔砖。当田晓霞在下面喊他时,他都惊呆了——这家伙怎找到这儿来了?楼上所有的民工都停止了手中的活,惊讶地朝下面观望。他们大概弄不明白,这么个花朵一般的“洋”姑娘,怎来找浑身糊着泥巴的揽工小子孙少平呢?她是他的什么人?有的工匠立刻和孙少平开起了粗俗不堪的玩笑。孙少平很难堪地从脚手架上溜下来,搓着手上的泥巴,走到田晓霞面前。晓霞立刻对他说明了来意。孙少平听后,犹豫了一会,说:“既然养民盛情邀请,我得去一下,什么时候?”
“今天晚上,你把金波也叫上,我在学校门口等你们。”
“那好吧!你要不要去一下我住的地方?”
少平抬头望了望脚手架,见所有的工匠仍然不干活,站下“观赏”他们。他脸通红,说:“不,我很高兴,甚至还有点……骄傲!”晓霞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她也红了脸,说:“那我就先走了,你们可一定要来啊……”少平就替她推着自行车,走过坑坑洼洼的建筑工地,一直把她送到柴油机厂大门口。送走晓霞后,少平的心仍然突突地跳着。真的,他高兴,也有些得意。晓霞来这样的地方找他,让与他一起干活的工匠们羡慕不已,这使他感到一种男人虚荣心的极大满足,至于到顾养民家里去聚会,那倒是一件十分平常的事了。他返回工地,给站场的工头请了假,就先到他的住处去换了身干净衣服,便动身去东关找金波。
金波听说顾养民请他们去吃饭,既意外又有点作难。我们知道,高中时为少平和红梅的事,他曾策划和组织了那次打顾养民的事件。虽然这事已经过了好几年,但仍然记忆犹新。他于是对少平说:“我还是不去了。你一个人去,就说你没找见我……”少平笑了,说:“还为过去那事吗?咱们现在都不是小孩了,顾养民也不会计较这些事,否则他不会邀请咱们。咱们不去,反倒失了风格。”金波想了一下,说:“那就去吧!”于是,这两个人在下午五点钟左右,一块相跟着去了北关的黄原师专。
晓霞早已在学校大门口笑吟吟地等待他们了。三个人进了顾养民家。养民兴奋地拉住他们的手摇了半天。他和保姆一块动手,早已经准备好了一桌饭菜。他还把父亲的小酒柜打开,把所有的白酒、红酒、啤酒都拿了出来。四个老同学围着桌子先后落座。亲切、兴奋,又有点百感交集。几年前,他们还是少年。现在却都成了大人,而且每个人都已经有过一些生活的经历。当年,他们还为一些事闹过孩子式的别扭。现在想起来,连这些别扭都值得人怀恋!中学时代的生活啊,将永远鲜活地保持在每个人一生的记忆之中。即使我们进入垂暮之年,我们也常常会把记忆的白帆,驶回到那些金色的年月里……
“干杯!”四个人把酒杯碰在了一起。他们一边喝酒,一边热烈地交谈着。当然,话题一开始总要回首往事的。只不过,三个男人都小心翼翼,谁也不提起郝红梅的名字——唉,你们呀!你们大概只知道可怜的红梅结婚了,可是她怎样悲惨地生活着你们知道吗?你们难道都忘记了这个不幸的人吗?不,也许他们谁都没有忘记这个人,只是这个场所不宜谈论她罢了。保姆开始上热菜。顾养民有素养地把菜分别夹到每个人面前的小碟里。四个命运不尽相同的同学这顿饭吃得很融洽。顾养民和田晓霞觉得,尽管孙少平和金波目前都没有工作,但在他们面前一点也不自卑,而且言辞谈吐和对生活的见解,并不比他们低。尤其是孙少平,思想和眼界都很开阔,有些观点使两个大学生都有点震惊。在少平和金波这方面看来,顾养民和田晓霞虽然进了大学门,在他们面前也不自视骄傲,像对待真正的朋友那样诚恳和尊重。几杯酒下肚,四个人的情绪高昂起来。晓霞提议一人唱一支歌。他们四个人曾经一块参加过中学的文艺宣传队,这方面都是人才,便立刻响应晓霞的建议,开始再一次重温过去的快乐。晓霞带头先唱了电影《冰山上的来客》中的两支插曲。接着金波唱了他最动情的《在那遥远的地方》——直唱得自己泪花子在眼里打转。少平和养民合唱了深沉的美国民歌《老人河》……
噢,年轻的朋友们,你们是不是还会重演一次过去那样的爱情之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