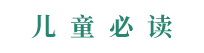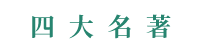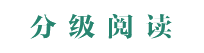孙少平径直来到与采掘区队办公室相连的浴池,开始了下井的第一道程序——换工作衣。由许多小柜组成的一排排大作衣柜就立在水池旁边。一人占一个小柜,钥匙自带。整个浴池为三层楼,每层的格局大同小异。少平的作衣柜在三楼。现在,中午十二点入坑的工人,正陆续走上地面。他们在通往井口那条暗道旁的矿灯房交了灯具,就纷纷进了浴池。这些人疲倦得连说话的气力也没有,沉默寡言地把又黑又脏的作衣脱下。有的人立刻跳进黑糊糊的热水池,舒服得“啊啊”地呻吟。有的人先忙着过烟瘾,光屁股倒在作衣柜前,或蹲在浴池的磁砖楞上。所有的人都是两支烟衔接在一起,到处听得见“咝咝”的吸气、“扑扑”的吹气以及疲劳的叹息声。整个大厅里弥漫着白雾般的水蒸气和臭烘烘的尿臊味。
少平换好工作衣,就从浴池的楼上走下来,在一楼矿灯房的小窗口,把灯牌扔进去。接着,便有一只女人的手把他的矿灯递出来。矿灯房四壁堵得像牢房一般严实,只留几个小口口。里面全是女工——一般都是丈夫因公伤之后顶替招工的。煤矿的女人太少了,就是这几个寡妇,也常是矿工们在井下猥狎地百谈不厌的话题。她们被四堵水泥墙保护得严严实实,以免遭受某些鲁莽之徒的攻击。男人们只能每天两次看看她们的手。少平从那只女人手里接过自己的矿灯,把灯绳往腰里一束,就提着灯盏穿过暗道,向井口走去。暗道本来有灯,但早被人用斧头打掉了。如果再安,不出一天照样会被打掉。疲劳的工人常常冒出许多无名火而无处发泄,不时随手搞点小小的破坏。穿过暗道的尽头,准备下井的工人从井口一直涌到了那几十个水泥台阶上。人们到这里仍然是沉默寡言,只听见上下罐的信号铃在当啷当啷地响着。
十分钟后,少平便下到井底。接着,在黑暗的坑道中步行近一个小时(其间要上下爬四五道大坡),才来到他们班的工作面上。头茬炮还没有放。所有的斧子工和攉煤工都在溜子机尾的一个拐巷里等待。人们在黑暗中坐着,或干脆大叉腿睡在煤堆里。正像农民在山里不嫌土,煤矿工人也不嫌煤,什么地方都可以躺下睡——反正这地方谁也别想把衣服穿干净!这一段时光实在叫人闲很慌。矿工一下井,就想马上干活。每天的任务都是死的,干完才能上井,那么最好早点就干。但井下的工作程序也是死的,没有放炮,想干也干不成!在这个时候,人们既然闲得没事,又不能抽烟,总得寻找某种消遣方式。最好的消遣方式当然是议论女人。首先从矿灯房小窗口那只女人的手谈起,一直谈到和自己的老婆睡觉和各种粗俗不堪的细节。人们在黑暗中猥狎地说笑着,微弱的矿灯光照出一张张露着白牙的嘴巴。
通常这个时候,少平总是把随身带下井的一本书在黑暗中翻到折页的地方,然后借用手中的矿灯光,一声不吭地看起来。最近他看的是《红与黑》。这本书他以前粗粗翻过。印象不深,因此想再看一遍。
“外国人也是人!他们的故事咱们正听得少!你说!”
“外国的男人女人一见面就一个啃一个,正美!”安锁子喊叫。
既然班长提议,大伙都想听,少平只好给他们讲起了《红与黑》的故事。于连这个名字像中国人的名字,大家能记下,其他人物的名字他都用什么“先生”、“夫人”、“小姐”等代替了。
今天,大家躺在黑暗的煤堆里,又准备听他讲于连的故事。孙少平尽管今晚心情不太好,但他还是在煤溜子的隆隆声中,接着昨天的情节给大伙讲开了。今天该讲于连怎样爬着那个梯子,从窗口钻进了“小姐”的卧室。当少平绘声绘色地讲到于连爬进窗户,抱住那位“小姐”的时候,安锁子突然像发情的公牛那般嚎叫了一声,便从少平手中夺过那本书,一扬手扔在了煤溜子上:“去它妈的!于连小子×美了,老子在这儿干受罪!”少平还没反应过来,那本《红与黑》就被溜子拉走了。于连、“夫人”、“小姐”,以及整个巴黎的上流社会,都埋进煤堆,滚进了机头那边的溜煤眼。
安锁子的举动引起黑暗中一片快活的哄堂大笑。少平无可奈何,一本书的毁灭引得大家一笑,那也许就是值得的?无聊而寂寞的人们呀!疯狂的安锁子做完这件破坏性的工作,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把裤子一脱,光屁股蹲在一边就拉开了屎。“我造你亲妈!你不能往远一点吗?”王世才骂道。那边只传来“嘿”一声无耻的笑。少平知道,安锁子已经三十岁的人了,还没找下老婆,因此一听男欢女爱,就忍不住变态似的发狂。唉,去它妈的!书毁就毁了,他只能另买一本。
这时,掌子面那边接连响起沉重的爆炸声。顿刻间,浓烟就灌满了巷道。有人破着嗓子咳嗽起来。炮声一停,王世才像只老虎一般跳起来,喊叫大家赶快进工作面!于是,那天天照旧的惊险的场面便又展开了……接连攉完三荐炮炸下的煤,他们一个个累得像死人一般。众人先后摇摇晃晃通过黑暗的巷道,向井口走去——此刻,地面上又该是阳光灿烂的时候了。
“我没见你出来……怎啦?”王世才用手在他头上摸了摸。“你病了……站起走吧!”师傅架着胳膊把他从地上拉起来。一股热辣辣的激流涌上了孙少平的胸腔。他无声地立起来,依靠着师傅的肩膀,走出了风门。
上井后,少平在师傅的帮助下洗了一个热水澡,感到稍有好转,但还不可能退烧。“走,到我家里去。你是着了凉,吃点热呼饭,再睡一觉,就屁的事也没了!”王世才换完衣服,硬把他拉起身。他只好随着师傅出了大门,从压风房那边的小坡上拐上去,沿着铁路向师傅家走去。一路上,王世才一直架着他的一条胳膊。到家后,王世才马上叫老婆单另给他做一碗酸辣面条。我们知道,这个家少平已经来过一次。那时他是一个想要点醋的生人。如今,他们已经成师徒关系了。王世才的老婆叫惠英,像所有矿工的老婆一样,对男人关照的体贴入微。她早已把菜炒好,细心地用碗扣在炉边上。她一边招呼少平吃药,一边开始侍候男人喝酒吃饭。少平的面条做好后,明明抢着要自己端给孙叔叔。惠英只好在后面像老母鸡一样护架着他,生怕把孩子烫了。王世才一边喝酒,一边看着她母子俩不由满足地“嘿嘿”笑着。
当少平从这母子俩手中接过热烫烫的一碗面条时,泪花子在眼眶里直打转。他没有想到,在远离故乡的地方他受到了这种亲人般的关照。吃完饭,少平就准备回他自己的宿舍去,但一家三口人都不让他走。王世才夫妇拉扯着把他带到旁边的屋子里,给他安顿好床铺。他们在他身子压了三床棉被,还在屋里生起了火。
惠英也笑着说:“到这里就不要见外。你王大哥常回来夸你,说你有文化,还能吃下煤矿的苦。以后你常跟你哥回来!大灶上的饭没法吃!你说嫂子的饭怎样?”
“好!”少平说。
王世才手在老婆的屁股蛋上拍了一巴掌,说:“甭自夸自了!”
“别打我妈!”明明喊叫着,用他的小手报复似地在他爸爸的屁股上也拍了一巴掌,使得三个大人都忍不住大笑起来。“今天你能喝酒了,好好陪你哥喝两杯!”惠英说着,便在两个大玻璃杯中倒满了白酒。这是煤矿工人喝酒的气度——不用小盅,而用城里人喝茶的大杯。在潮湿阴冷的井下干八九个小时的活,上地面来灌一两杯烧酒那是再好不过了;它使人晕晕乎乎,忘记疲劳,忘记惊心动魄的掌子面。
少平在喝酒的时候才知道,明天是明明的生日——小家伙要满六岁了。他寻思得给孩子买个什么礼物。他问明明:“你最喜欢什么?”
对,他记起商店里有一种绒毛做的玩具狗,挺大,挺威风。就给他买这件礼物吧!吃完饭,王世才没有睡觉,说他要到矸山上捡点烧饭的煤去。
少平立刻说:“我跟你一块去!”
“你不要去,你病刚好。”惠英说。
“要去就去。”王世才不阻挡他。
于是,师徒俩就一块相跟着出了门,向矸石山走去。少平担着筐子,师傅背抄着手走在后边。对于大部分黑户人口的矿工来说,尽管他们生活在一个煤的世界,整天都在挖煤,但他们自己的煤却不那么容易搞到。他们当然不想出钱买煤,只好利用上井休息的空隙,到矸石山的矸石中间去捡一些碎小的煤块。这同样是一件很苦的事。在矸石山的陡坡上,人连站也站不住,而上面的矸石还在不断哗哗往下飞滚,不小心就会被砸得头破血流!
“我在井下已经干了十几年,被矸石打掉两颗门牙,身上的伤疤数也数不清。有时我累得的确不想下井了。可是,每当我晚上趴在你嫂子的肚皮上,我想,这么好的女人,还给我生了这么好的儿子,可他们要吃饭呀!所以,第二天起来就又钻到地下了。你如果有老婆,就明白我说的这些话了……你现在没有?赶紧找一个!煤矿这么苦的话,没个老婆可是不行啊……”。
少平静静地听着,眼睛一直望着远方的山峦。他没有回答师傅的问话,而心里却想着晓霞。此刻,他的心是冰凉的。晓霞!晓霞!现在我越来越明白,我们是不可能在一块生活了。无疑,我的一生,就要在这里度过。而你将永远是大城市的一员。我决不可能生活在你那个世界里;可是,你又怎能到我这个世界来生活呢?不可能!你不可能像惠英一样,到这样一个地方来侍候一个煤矿工人,你恐怕连到这里看一看的愿望都没有!
他们在这里蹲了一会,少平便担起煤筐,师傅背抄着手跟在他后边,两个人相跟着慢慢走下山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