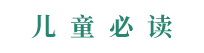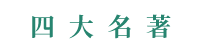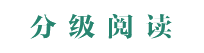景--周宅客厅内。半夜两点钟的光景。
开幕时,周朴园一人坐在沙发上,读文件;旁边燃着一个立灯,四周是黑暗的。外面还隐隐滚着雷声,雨声淅沥可闻,窗前帷幕垂了下来,中间的门紧紧地掩了,由门上玻璃望出去,花园的景物都掩埋在黑暗里,除了偶尔天空闪过一片耀目的电光,蓝森森的看见树同电线杆,一瞬又是黑漆漆的。
朴 (放下文件,呵欠,疲倦地伸一伸腰)来人啦!(取眼镜,擦目,声略高)来人!(擦眼镜,走到左边饭厅门口,又恢复平常的声调)这儿有人么?(外面闪电,停,走到右边柜前,按铃。无意中又望见侍萍的相片,拿起,戴上眼镜看。)
[仆人上。]
仆 爷!
朴 我叫了你半天。
仆 外面下雨,听不见。
朴 (指钟)钟怎么停了?
仆 (解释地)每次总是四凤上的,今天她走了,这件事就忘了。
朴 什么时候了?
仆 嗯——大概有两点钟了。
朴 刚才我叫帐房汇一笔钱到济南去,他们弄清楚没有?
仆 您说寄给济南一个,一个姓鲁的,是么?
朴 嗯。
仆 预备好了。
[外面闪电,朴园回头望花园。]
朴 萝架那边的电线,太太叫人来修理了么?
仆 叫了,电灯匠说下着大雨不好修理,明天再来。
朴 那不危险么?
朴 可不是么?刚才大少爷的狗走过那儿,碰着那根电线,就给电死了。现在那儿已经用绳子圈起来,没有人走那儿。
朴 哦。什么,现在几点了?
仆 两点多了。老爷要睡觉么?
朴 你请太太下来。
仆 太太睡觉了。
朴 (无意地)二少爷呢?
仆 早睡了。
朴 那么,你看看大少爷。
仆 大少爷吃完饭出去,还没有回来。
[沉默半晌。]
朴 (走回沙发坐下,寂寞地)怎么这屋子一个人也没有
仆 是,老爷,一个人也没有。
朴 今天早上没有一个客来。
仆 是,老爷。外面下着很大的雨,有家的都在家里呆着。
朴 (呵欠,感到更深的空洞)家里的人也只有我一个人还在醒着。
仆 是,差不多都睡了。
朴 好,你去吧。
仆 您不要什么东西么?
朴 我不要什么。
[仆人由中门下,朴园站起来,在厅中来回沉闷地踱着,又停在右边柜前,拿起侍萍的相片。开了中间的灯。冲由饭厅上。]
冲 (没想到父亲在这儿)爸!
朴 (露喜色)你——你没有睡?
冲 嗯。
朴 找我么?
冲 不,我以为母亲在这儿。
朴 (失望)哦——你母亲在楼上。
冲 没有吧,我在她的门上敲了半天,她的门锁着。是的,那也许。爸,我走了。
朴 冲儿,(冲立)不要走。
冲 爸,您有事?
朴 没有。(慈爱地)你现在怎么还不睡?
冲 (服从地)是,爸,我睡晚了,我就睡。
朴 你今天吃完饭把克大夫给的药吃了么?
冲 吃了。
朴 打了球没有?
冲 嗯。
朴 快活么?
冲 嗯。
朴 (立起,拉起他的手)为什么,你怕我么?
冲 是,爸爸。
朴 (干涩地)你像是有点不满意我,是么?
冲 (窘迫)我,我说不出来,爸。
[半晌。朴园走回沙发,坐下叹一口气。招冲来,冲走近。]
朴 (寂寞地)今天——呃,爸爸有一点觉得自己老了。(停)你知道么?
冲 (冷淡地)不,不知道,爸。
朴 (忽然)你怕你爸爸有一天死了,没有人照顾你,你不怕么?
冲 (无表情地)嗯,怕。
朴 (想自己的儿子亲近他,可亲地)你今天早上说要拿你的学费帮一个人,你说说看,我也许答应你。
冲 (悔怨地)那是我糊涂,以后我不会这样说话了。
[半晌。]
朴 (恳求地)后天我们就搬新房子,你不喜欢么?
冲 嗯。
[半晌。]
朴 (责备地望着冲)你对我说话很少。
冲 (无神地)嗯,我——我说不出,您平时总像不愿意见我们似的。(嗫嚅地)您今天有点奇怪,我——我——
朴 (不愿他向下说)嗯,你去吧!
冲 是,爸爸。
[冲由饭厅下。朴园失望地看着他儿子下去,立起,拿起侍萍的相片,寂寞地呆望着四周。关上立灯,面前书房。]
[繁漪由中门上。不做声地走进来,雨衣上的是还在往下滴,发鬓有些湿。颜色是很惨白,整个面都像石膏的塑像。高而白的鼻梁,薄而红的嘴唇死死地刻在脸上,如刻在一个严峻的假面上,整个脸庞是无表情的。只有她的眼睛烧着心内疯狂的火,然而也是冷酷的,爱和恨烧尽了女人一切的仪态,她像是厌弃了一切,只有计算着如何报复的心念在心中起伏。她看见朴园,他惊愕地望着她。]
繁 (毫不奇怪地)还没睡么?(立在中门前,不动。)
朴 你?(走近她,粗而低的声音)你上哪儿去了?(望着她,停)冲儿找你一个晚上。
繁 (平常地)我出去走走。
朴 这样大的雨,你出去走?
繁 嗯,(忽然报复地)我有神经病。
朴 我问你,你刚才在哪儿?
繁 (厌恶地)你不用管。
朴 (打量她)你的衣服都湿了,还不脱了它。
繁 (冷冷地,有意义地)我心里发热,我要在外面冰一冰。
朴 (不耐烦地)不要胡言乱话的,你刚才究竟上哪儿去了?
繁 (无神地望着他,清楚地)在你的家里!
朴 (烦恶地)在我的家里?
繁 (觉得报复的快感,微笑)嗯,在花园里赏雨。
朴 一夜晚。
繁 (快意地)嗯,淋了一夜晚。
[半晌,朴园惊疑地望着她,繁漪像一座石像似的仍站在门前。]
朴 漪,我看你上楼去歇一歇吧。
繁 (冷冷地)不,不,(忽然)你拿的什么?(轻蔑地)哼,又是那个女人的相片!(伸手拿)。
朴 你可以不看,萍儿的母亲的。
繁 (抢过去了,前走了两步,就向灯下看)萍儿的母亲很好看。
[朴园没有理她,在沙发上坐下。]
繁 问你,是不是?
朴 嗯。
繁 样子很温存的。
朴 (眼睛望着前面)
繁 她很聪明。
朴 (冥想)嗯。
繁 (高兴地)真年青。
朴 (不自觉地)不,老了。
繁 (想起)她不是早死了么?
朴 嗯,对了,她早死了。
繁 (放下相片)奇怪,我像是在哪儿见过似的。
朴 (抬起头,疑惑地)不,不会吧。你在哪儿见过她吗?
繁 (忽然)她的名字很雅致,侍萍,侍萍,就是有点丫头气。
朴 好,我看还睡去吧。(立起,把相片拿起来。)
繁 拿这个做什么?
朴 后天搬家,我怕掉了。
繁 不,不,(从他手中取过来)放在这儿一晚上,(怪样地笑)不会掉的,我替你守着她。(放在桌上)
朴 不要装疯!你现在有点胡闹!
繁 我是疯了。请你不用管我。
朴 (愠怒)好,你上楼去吧,我要一个人在这儿歇一歇。
繁 不,我要一个人在这儿歇一歇,我要你给我出去。
朴 (严厉地)繁漪,你走,我叫你上楼去!
繁 (轻蔑地)不,我不愿意。我告诉你(暴躁地)我不愿意!
[半晌。]
朴 (低声)你要注意这儿,(指头)记着克大夫的话,他要你静静地,少说话。明天克大夫还来,我已经替你请好了。
繁 谢谢你!(望着前面)明天?哼!
[萍低头由饭厅走出,神色忧郁,走向书房。]
朴 萍儿。
萍 (抬头,惊讶)爸!您还没有睡。
朴 (责备地)怎么,现在才回来。
萍 不,爸,我早回来,我出去买东西去了。
朴 你现在做什么?
萍 我到书房,看看爸写的介绍信在那儿没有。
朴 你不是明天早车走么?
萍 我忽然想起今天夜晚两点半钟有一趟车,我预备现在就走。
繁 (忽然)现在?
萍 嗯。
繁 (有意义地)心里就这样急么?
萍 是,母亲。
朴 (慈爱地)外面下着大雨,半夜走不大方便吧?
萍 这时走,明天日初到,找人方便些。
朴 信就在书房桌上,你要现在走也好。(萍点头,走向书房)你不用去!(向繁漪)你到书房把信替他拿来。
繁 (看朴园,不信任地)嗯!
[繁漪进书房。]
朴 (望繁出,谨慎地)她不愿上楼,回头你先陪她到楼上去,叫底下人伺候她睡觉。
萍 (无法地)是,爸爸。
朴 (更小心)你过来!(萍走近,低声)告诉底下人,叫他们小心点,(烦恶地)我看她的病更重,刚才她忽然一个人出去了。
萍 出去了?
朴 嗯。(严厉地)在外面淋了一夜晚的雨,说话也非常奇怪,我怕这不是好现象。(觉得恶兆来了似的)我老了,我愿意家里平平安安地……
萍 (不安地)我想爸爸只要把事不看得太严重了,事情就会过去的。
朴 (畏缩地)不,不,有些事简直是想不到的。天意很——有点古怪:今天一天叫我忽然悟到为人太——太冒险,太——太荒唐:(疲倦地)我累得很。(如释重负)今天大概是过去了。(自慰地)我想以后——不该,再有什么风波。(不寒而栗地)不,不该!
[繁漪持信上。]
繁 (嫌恶地)信在这儿!
朴 (如梦初醒,向萍)好,你走吧,我也想睡了。(振起喜色)嗯!后天我们一定搬新房子,你好好地休息两天。
繁 (盼望他走)嗯,好。
[朴园由书房下。]
繁 (见朴园走出,阴沉地)这么说你是一定要走了。
萍 (声略带愤)嗯。
繁 (忽然急躁地)刚才你父亲对你说什么?
萍 (闪避地)他说要我陪你上楼去,请你睡觉。
繁 (冷笑)他应当叫几个人把我拉上去,关起来。
萍 (故意装作不明白)你这是什么意思?
繁 (迸发)你不用骗我。我知道。我知道,(辛酸地)他说我是神经病。疯子,我知道他,要你这样看我,他要什么人都这样看我。
萍 (心悸)不,你不要这样想。
繁 (奇怪的神色)你?你也骗我?(低声,阴郁地)我从你们的眼神看出来,你们父子都愿我快成疯子!(刻毒地)你们——父亲同儿子——偷偷在我背后说冷话,说我,笑我,在我背后计算着我。
萍 (镇静自己)你不要神经过敏,我送你上楼去。
繁 (突然地,高声)我不要你送,走开!(抑制着,恨恶地,低声)我还用不着你父亲偷偷地,背着我,叫你小心,送一个疯子上楼。
萍 (抑制着自己的烦嫌)那么,你把信给我,让我自己走吧。
繁 (不明白地)你上哪儿?
萍 (不得已地)我要走,我要收拾我的东西。
繁 (忽然冷静地)我问你,你今天晚上上哪儿去了?
萍 (敌对地)你不用问,你自己知道。
繁 (低声,恐吓地)到底你还是到她那儿去了。
[半晌,繁漪望萍,萍低头。]
萍 (断然,阴沉地)嗯,我去了,我去了,(挑战地)你要怎么样?
繁 (软下来)不怎么样。(强笑)今天下午的话我说错了,你不要怪我。我只问你走了以后,你预备把她怎么样?
萍 以后?(冒然地)我娶她!
繁 (突如其来地)娶她?
萍 (决定地)嗯。
繁 (刺心地)父亲呢?
萍 (淡然)以后再说。
繁 (神秘地)萍,我现在给你一个机会。
萍 (不明白)什么?
繁 (劝诱他)如果今天你不走,你父亲那儿我可以替你想法子。
萍 不必,这件事我认为光明正大,我可以跟任何人谈。她——她不过就是穷点。
繁 (愤然)你现在说话很像你的弟弟。(忧郁地)萍!
萍 干什么?
繁 (阴郁地)你知道你走了以后,我会怎么样?
萍 不知道。
繁 (恐惧地)你看看你的父亲,你难道想象不出?
萍 我不明白你的话。
繁 (指自己的头)就在这儿:你不知道么?
萍 (似懂非懂地)怎么讲?
繁 (好像在叙述别人的事情)第一,那位专家,克大夫免不了会天天来的,要我吃药,逼着我吃药,吃药,吃药,吃药!渐渐伺候着我的人一定多,守着我,像个怪物似的守着我。他们——
萍 (烦)我劝你,不要这样胡想,好不好?
繁 (不顾地)他们渐渐学会了你父亲的话,“小心,小心点,她有点疯病!”到处都偷偷地在我背后低着声音说话,叽咕着,慢慢地无论谁都要小心点,不敢见我,最后铁链子锁着我,那我真成了疯子。
萍 (无办法)唉!(看表)不早了,给我信吧,我还要收拾东西呢。
繁 (恳求地)萍,这不是不可能的。(乞怜地)萍,你想一想,你就一点——就一点无动于衷么?
萍 你——(故意恶狠地)你自己要走这一条路,我有什么办法?
繁 (愤怒地)什么,你忘记你自己的母亲也被你父亲气死的么?
萍 (一了百了,更狠毒地激惹她)我母亲不像你,她懂得爱!她爱自己的儿子,她没有对不起我父亲。
繁 (爆发,眼睛射出疯狂的火)你有权利说这种话么?你忘了就在这屋子,三年前的你么?你忘了你自己才是个罪人:你忘了,我们——(突然,压制自己,冷笑)哦,这是过去的事,我不提了。(萍低头,身发颤,坐沙发上,悔恨抓着他的心,面上筋肉成不自然的痉挛。她转向他,哭声,失望地说着)哦,萍,好了。这一次我求你,最后一次求你。我从来不肯对人这样低声下气说话,现在我求你可怜可怜我,这家我再也忍受不住了。(哀婉地诉出)今天这一天我受的罪过你都看见了,这样子以后不是一天,是整月,整年地,以至到我死,才算完。他厌恶我,你的父亲:他知道我明白他的底细,他怕我。他愿意人人看我是怪物,是疯子,萍!
萍 (心乱)你,你别说了。
繁 (急迫地)萍,我没有亲戚,没有朋友,没有一个可信的人,我现在求你,你先不要走——
萍 (躲闪地)不,不成。
繁 (恳求地)即使你要走,你带我也离开这儿——
萍 (恐惧地)什么。你简直胡说!
繁 (恳求地)不,不,你带我走,带我离开这儿,(不顾一切地)日后,甚至于你要把四凤接来——一块儿住,我都可以,只要,只要(热烈地)只要你不离开我。
萍 (惊惧地望着她,退后,半晌,颤声)我——我怕你真疯了!
繁 (安慰地)不,你不要这样说话。只有我明白你,我知道你的弱点,你也知道我的。你什么我都清楚。(诱惑地笑,向萍奇怪地招着手,更诱惑地笑)你过来,你——你怕什么?
萍 (望着她,忍不住地狂喊出来)哦,我不要你这样笑!(更重)不要你这样对我笑!(苦恼地打着自己的头)哦,我恨我自己,我恨,我恨我为什么要活着。
繁 (酸楚地)我这样累你么?然而你知道我活不到几年了。
萍 (痛苦地)你难道不知道这种关系谁听着都厌恶么?你明白我每天喝酒胡闹就因为自己恨,恨我自己么?
繁 (冷冷地)我跟你说过多少遍,我不这样看,我的良心不是这样做的。(郑重地)萍,今天我做错了,如果你现在听我的话,不离开家;我可以再叫四凤回来的。
萍 什么?
繁 (清清楚楚地)叫她回来还来得及。
萍 (走到她面前,声沉重,慢说)你跟我滚开!
繁 (顿,又缓缓地)什么?
萍 你现在不像明白人,你上楼睡觉去吧。
繁 (明白自己的命运)那么,完了。
萍 (疲惫地)嗯,你去吧。
繁 (绝望,沉郁地)刚才我在鲁家看见你同四凤。
萍 (惊)什么,你刚才是到鲁家去了?
繁 (坐下)嗯,我在他们家附近站了半天。
萍 (悔惧)什么时候你在那里?
繁 (低头)我看着你从窗户进去。
萍 (急切)你呢?
繁 (无神地望着前面)就走到窗户前面站着。
萍 那么有一个女人叹气的声音是你么?
繁 嗯。
萍 后来,你又在那里站多半天?
繁 (慢而清朗地)大概是直等到你走。
萍 哦!(走到她身后,低声)那窗户是你关上的,是么?
繁 (更低的声音,阴沉地)嗯,我。
萍 (恨极,恶毒地)你是我想不到的一个怪物!
繁 (抬起头)什么?
萍 (暴烈地)你真是一个疯子!
繁 (无表情地望着他)你要怎么样?
萍 (狠恶地)我要你死!再见吧!
[萍由饭厅急走下,门猝然地关上。]
繁 (呆滞地坐了一下,望着饭厅的门。瞥见侍萍的相片,拿在手上,低叹,阴郁地)这是你的孩子!(缓缓扯下硬卡片贴的像纸,一片一片地撕碎。沉静地立起来,走了两步。)奇怪,心里安静的很!
[中门轻轻推开,繁漪回头,鲁贵缓缓地走进来。他的狡黠地的眼睛,望着她笑着。]
贵 (鞠躬,身略弯)太太,您好。
繁 (略惊)你来做什么?
贵 (假笑)跟您请安来了。我在门口等了半天。
繁 (镇静)哦,你刚才在门口?
贵 (低声)对了。(更神秘地)我看见大少爷正跟您打架,我——(假笑)我就没敢进来。
繁 (沉静地,不为所迫)你原来要做什么?
贵 (有把握地)原来我倒是想报告给太太,说大少爷今天晚上喝醉了,跑到我们家里去。现在太太既然是也去了,那我就不必多说了。
繁 (嫌恶地)你现在想怎么样?
贵 (倨傲地)我想见见老爷。
繁 老爷睡觉了,你要见他什么事?
贵 没有什么事,要是太太愿意办,不找老爷也可以。(着重,有意义地)都看太太要怎么样。
繁 (半晌,忍下来)你说吧,我也可以帮你的忙。
贵 (重复一遍,狡黠地)要是太太愿作主,不叫我见老爷,多麻烦(假笑)那就大家都省事了。
繁 (仍不露声色)什么,你说吧。
贵 (谄媚地)太太做了主,那就是您积德了。我们只是求太太还赏饭吃。
繁 (不高兴地)你,你以为我——(转缓和)好,那也没有什么。
贵 (得意地)谢谢太太。(伶俐地)那么就请太太赏个准日子吧。
繁 (爽快地)你们在搬了新房子后一天来吧。
贵 (行礼)谢谢太太恩典!(忽然)我忘了,太太,你没见着二少爷么?
繁 没有。
贵 您刚才不是叫二少爷赏给我们一百块钱么?
繁 (烦厌地)嗯?
贵 (婉转地)可是,可是都叫我们少爷回了。
繁 你们少爷?
贵 (解释地)就是大海——我那个狗食的儿子。
繁 怎么样?
贵 (很文雅地)我们的侍萍,实在还不知道呢。
繁 (惊,低声)侍萍?(沉下脸)谁是侍萍?
贵 (以为自己被轻视了,侮慢地)侍萍就是侍萍,我的家里的,就是鲁妈。
繁 你说鲁妈,她叫侍萍?
贵 (自夸地)她也念过书。名字是很雅气的。
繁 “侍萍”,那两个字怎么写,你知道么?
贵 我,我,(为难,勉强笑出来)我记不得了。反正那个萍字是跟大少爷名字的萍我记得是一样的。
繁 哦!(忽然把地上撕破的相片碎片拿起来对上,给他看)你看看,这个人你认不认识?
贵 (看了一会,抬起头)你认识,太太。
繁 (急切地)你认识的人没有一个像她的么?(略停)你想想看,往近处想。
贵 (抬头)没有一个,太太,没有一个。(突然疑惧地)太太,您怎么?
繁 (回想,自己疑惑)多半我是胡思乱想。(坐下)
贵 (贪婪地)啊,太太,您刚才不是赏我们一百块钱么?可是我们大海又把钱回了,你想——
[中门渐渐推开。]
贵 (回头)谁?
[大海由中门进,衣服俱湿,脸色阴沉,眼不安地向四面望,疲倦,愤恨在他举动里显明地露出来。繁漪惊讶地望着他。]
大 (向鲁贵)你在这儿!
贵 (讨厌他的儿子)嗯,你怎么进来的?
大 (冰冷)铁门关着,叫不开,我爬墙进来的。
贵 你现在来这儿干什么?不看看你妈找四凤怎么样了?
大 (用一块湿手巾擦着脸上的雨水)四凤没找着,妈在门外等着呢。(沉重地)你看见四凤了么?
贵 (轻蔑)没有,我没有看见,(觉得大海小题大做,烦恶地皱着眉毛)不要管她,她一回儿就会回家。(走近大海)你跟我回家去。周家的事情也办妥了,都完了,走吧!
大 我不走。
贵 你要干什么?
大 你也别走,你先跟我把这儿大少爷叫出来,我找不着他。
贵 (疑惧地,摸着自己的下巴)你要怎么样?我刚弄好,你是又要惹祸?
大 (冷静地)没有什么,我只想跟他谈谈。
贵 (不信地)我看你不对,你大概又要——
大 (暴躁地,抓着鲁贵的领口)你找不找?
贵 (怯弱地)我找,我找,你先放下我。
大 好,(放开他)你去吧。
贵 大海,你,你得答应我,你可是就跟大少爷说两句话,你不会——
大 嗯,我告诉你,我不是打架来的。
贵 真的?
大 (可怕地走到鲁贵的面前,低声)你去不去?
贵 我,我,大海,你,你——
繁 (镇静地)鲁贵,你去叫他出来,我在这儿,不要紧的。
贵 也好,(向大海)可是我请完大少爷,我就从那门走了,我,(笑)我有点事。
大 (命令地)你叫他们把门开开,让妈进来,领她在房里避一避雨。
贵 好,好,(向饭厅下)完了,我可有事,我就走了。
大 站住!(走前一步,低声)你进去,要是不找他出来就一人跑了,你可小心我回头在家里,哼!
贵 (生气)你,你,你,(低声,自语)这个小王八蛋!(没法子,走进饭厅下。)
繁 (立起)你是谁?
大 (粗鲁地)四凤的哥哥。
繁 (柔声)你是到这儿来找她么?你要见我们大少爷么?
大 嗯。
繁 (眼色阴沉沉)我怕他会不见你。
大 (冷静地)那倒许。
繁 (缓缓地)听说他现在就要上车。
大 (回头)什么!
繁 (阴沉地暗示)他现在就要走。
大 (愤怒地)他要跑了,他——
繁 嗯,他——
[萍由饭厅上,脸上有些慌,他看见大海,勉强地点一点头,声音略有点颤,他极力在镇静自己。]
萍 (向大海)哦!
大 好。你还在这儿。(回头)你叫这位太太走开,我有话要跟你一个人说。
萍 (望着繁漪,她不动,再走到她的面前)请您上楼去吧。
繁 好!(昂首由饭厅下)
[半晌。二人都紧紧握着拳,大海愤愤地望着他,二人不动。]
萍 (耐不住,声略颤)没想到你现在到这儿来。
大 (阴沉沉)听说你要走。
萍 (惊,略镇静,强笑)不过现在也赶得上,你来得还是时候,你预备怎么样?我已经准备好了。
大 (狠恶地笑一笑)你准备好了?
萍 (沉郁地望着他)嗯。
大 (走到他面前)你!(用力地击着萍的脸,方才的创伤又破,血向下流)
萍 (握着拳抑制自己)你,你,(忍下去,由袋内抽出白绸手绢擦脸上的血)
大 (切齿地)哼?现在你要跑了!
[半晌。]
萍 (压下自己的怒气,辩白地,故意用低沉的声音)我早有这个计划。
大 (恶狠地笑)早有这个计划?
萍 (平静下来)我以为我们中间误会太多。
大 误会?(看自己手上的血,擦在身上)我对你没有误会,我知道你是没有血性,只顾自己的一个十足的混蛋。
萍 (柔和地)我们两次见面,都是我性子最坏的时候,叫你得着一个最坏的印象。
大 (轻蔑地)不用推托,你是个少爷,你心地混帐!你们都是吃饭太容易,有劲儿不知道怎样使,就拿着穷人家的女儿开开心,完了事可以不负一点儿责任。
萍 (看出大海的神气,失望地)现在我想辩白是没有用的。我知道你是有目的而来的(平静地)你把你的枪或者刀拿出来吧。我愿意任你收拾我。
大 (侮蔑地)你会这样大方,在你家里,你很聪明!哼,可是你不值得我这样,我现在还不愿意拿我这条有用的命换你这半死的东西。
萍 (直视大海,有勇气地)我想你以为我现在怕你。你错了,与其说我怕你,不如说我怕我自己;我现在做错了一件事,我不愿意做错第二件事。
大 (嘲笑地)我看像你这种人活着就错了。刚才要不是我的母亲,我当时就宰了你!(恐吓地)现在你的命还在我的手心里。
萍 我死了,那是我的福气。(辛酸地)你以为我怕死,我不,我不,我恨活着,我欢迎你来。我够了,我是活厌了的人。
大 (厌恨地)哦,你活厌了,可是你还拉着我年青的糊涂妹妹陪着你,陪着你。
萍 (无法,强笑)你说我自私么?你以为我是真没有心肝,跟她开心就完了么?你问问你的妹妹,她知道我是真爱她。她现在就是我能活着的一点生机。
大
萍 (略顿)那就是我最恨的事情。我的环境太坏。你想想我这样的家庭怎么允许有这样的事。
大 (辛辣地)哦,所以你就可以一面表示你是真心爱她,跟她做出什么不要脸的事都可以,一面你还得想着你的家庭,你的董事长爸爸。他们叫你随便就丢掉她,再娶一个门当户对的阔小姐来配你,对不对?
萍 (忍耐不下)我要你问问四凤,她知道我这次出去,是离开了家庭,设法脱离了父亲,有机会好跟她结婚的。
大 (嘲弄)你推得好。那么像你深更半夜的,刚才跑到我家里,你怎样推托呢?
萍 (迸发,激烈地)我所说的话不是推托,我也用不着跟你推托,我现在看你是四凤的哥哥,我才这样说。我爱四凤,她也爱我,我们都年青,我们都是人,两个人天天在一起,结果免不了有点荒唐。然而我相信我以后会对得起她,我会娶她做我的太太,我没有一点亏待她的地方。
大 这么,你反而很有理了。可是,董事长大少爷,谁相信你会爱上一个工人的妹妹,一个当老妈子的穷女儿?
萍 (略顿,嗫嚅)那,那——那我也可以告诉你。有一个女人逼着我,激成我这样的。
大 (紧张地,低声)什么,还有一个女人?
萍 嗯,就是你刚才见过那位太太。
大 她?
萍 (苦恼地)她是我的继母!——哦,我压在心里多少年,我当谁也不敢说——她念过书,她受了很好的教育,她,她——她看见我就跟我发生感情,她要我——(突停)那自然我也要负一部分责任。
大 四凤知道么?
萍 她知道,我知道她知道。(含着苦痛的眼泪,苦闷地)那时我太糊涂,以后我越过越怕,越恨,越厌恶。我恨这中不自然的关系,你懂么?我要离开她,然而她不放松我。她拉着我,不放我,她是个鬼,她什么都不顾忌。我真活厌了,你明白么?我喝酒,胡闹,我只要离开她,我死都愿意。她叫我恨一切受过好教育,外面都装得正经的女儿。过后我见着四凤,四凤叫我明白,叫我又活了一年。
大 (不觉吐出一口气)哦!
萍 这些话多少年我对谁也说不出的,然而(缓慢地)奇怪,我忽然跟你说了。
大 (阴沉地)那大概是你父亲的报应。
萍 (没想到,厌恶地)你,你胡说!(觉得方才太冲动,对一个这么不相识的人说出心中的话。半晌,镇静下,自己想方才突出的原因,忽然,慢慢地)我告诉你,因为我认你是四凤的哥哥,我要你相信我的诚心,我没有一点骗她。
大 (略露善意)那么你真心预备要四凤么?你知道四凤是个傻孩子,她不会再嫁第二个人。
萍 (诚恳地)嗯,我今天走了,过了一两个月,我就来接她。
大 可是董事长少爷,这样的话叫人相信么?
萍 (由衣袋取出一封信)你可以看这封信,这是我刚才写给她的,就说的这件事。
大 (故意闪避地)用不着给我看,我——没有功夫!
萍 (半晌,抬头)那我现在没有什么旁的保证,你口袋里那件杀人的家伙是我的担保。你再不相信我,我现在人还是在你手里。
大 (辛酸地)周大少爷,你想这样就完了么?(恶狠地)你觉得我真愿意我的妹妹嫁给你这种东西么?(忽然拿出自己的手枪来)
萍 (惊慌)你要怎么样?
大 (恨恶地)我要杀了你,你父亲虽坏,看着还顺眼。你真是世界上最用不着,没有劲的东西。
萍 哦。好,你来吧!(骇惧地闭上目)
大 可是——(叹一口气,递手枪与萍)你还是拿去吧。这是你们矿上的东西。
萍 (莫明其妙地)怎么?(接下枪)
大 (苦闷地)没有什么。老太太们最糊涂。我知道我的妈。我妹妹是她的命。只要你能够叫四凤好好地活着,我只好不提什么了。
[萍还想说话,大海挥手,叫他不必再说,萍沉郁地到桌前把枪放好。]
大 (命令地)那么请你把我的妹妹叫出来吧。
萍 (奇怪)什么?
大 四凤啊——她自然在你这儿。
萍 没有,没有。我以为她在你们家里呢。
大 (疑惑地)那奇怪,我同我妈在雨里找了她两个多钟头,不见她。我想自然在这儿。
萍
大 (肯定地)半夜里她会到哪儿去?
萍 (突然恐惧)啊,她不会——(坐下呆望)
大 (明白)你以为——不,她不会,(轻蔑地)我想她没有这个胆量。
萍 (颤抖地)不,她会的,你不知道她。她爱脸,她性子强,她——不过她应当先见我,她(仿佛已经看见她溺在河里)不该这样冒失。
[半晌。]
大 (忽然)哼,你装得好,你想骗过我,你?她在你这儿!她在你这儿!
[外面远处口哨声。]
萍 (以手止之)不,你不要嚷。(哨声近,喜色)她,她来了,我听见她!
大 什么?
萍 这是她的声音,我们每次见面,是这样的。
大 她在这儿?
萍 大概就在花园里?
[萍开窗吹哨,应声更近。]
萍 (回头,眼含着眼泪,笑)她来了!
[中门敲门声。]
萍 (向大海)你先暂时在旁边屋子躲一躲,她没想到你在这儿。我想她再受不得惊了。
[忙引大海至饭厅门,大海下。]
外面的声音 (低)萍!
萍 (忙跑至中门)凤儿!(开门)进来!
[四凤由中门进,头发散乱,衣服湿透,眼泪同雨水流在脸上,眼角黏着淋漓的鬓发,衣裳贴着皮肤,雨后的寒冷逼着她发抖,她的牙齿上下地震战着。她见萍如同失路的孩子再见着母亲呆呆地望着他。]
四 萍!
萍 (感动地)凤!
四 (胆怯地)没有人儿?
萍 (难过,怜悯地)没有。(拉着她的手)
四 (放胆地)哦!萍!(抱着萍抽咽)
萍 (如许久未见她)你怎样,你怎样会这样?你怎样会找着我?(止不住地)你怎样进来的?
四 我从小门偷进来的。
萍 凤,你的手冰凉,你先换一换衣服。
四 不,萍,(抽咽)让我先看看你。
萍 (引她到沙发。坐在自己一旁,热烈地)你,你上哪儿去了,凤?
四 (看着他,含着眼泪微笑)萍,你还在这儿,我好像隔了多年一样。
萍 (顺手拿起沙发上的一条紫线毯给她围上)我可怜的凤儿,你怎么这样傻,你上哪儿去了?我的傻孩子!
四 (擦着眼泪,拉着萍的手,萍蹲在旁边)我一个人在雨里跑,不知道自己在哪儿。天上打着雷,前面我只看见模模糊糊的一片;我什么都忘了,我像是听见妈在喊我,可是我怕,我拼命地跑,我想找着我们门口那一条河跳。
萍 (紧握着四凤的手)凤!
四 可是不知怎么绕来绕去我总找不着。
萍 哦,凤,我对不起你,原谅我,是我叫你这样,你原谅我,你不要怨我。
四 萍,我怎样也不会怨你的,我糊糊涂涂又碰到这儿,走到花园那电线杆底下,我忽然想死了。我知道一碰那根电线,我就可以什么都忘了。我爱我的母亲,我怕我刚才对她起誓,我怕她说我这么一声坏女儿,我情愿不活着。可是,我刚要碰那根电线,我忽然看见你窗户的灯,我想到你在屋子里。哦,萍,我突然觉得,我不能就这样就死,我不能一个人死,我丢不了你。我想起来,世界大得很,我们可以走,我们只要一块儿离开这儿。萍啊,你——
萍 (沉重地)我们一块儿离开这儿?
四 (急切地)就是这一条路,萍,我现在已经没有家,(辛酸地)哥哥恨死我,母亲我没有脸见的。我现在什么都没有,我没有亲戚,没有朋友,我只有你,萍(哀告地)你明天带我去吧。
[半晌。]
萍 (沉重地摇着头)不,不——
四 (失望地)萍!
萍 (望着她,沉重地)不,不——我们现在就走。
四 (不相信地)现在就走?
萍 (怜惜地)嗯,我原来打算一个人现在走,以后再来接你,不过现在不必了。
四 (不信地)真的,一块儿走么?
萍 嗯,真的。
四 (狂喜地,扔下线毯,立起,亲萍的手,一面擦着眼泪)真的,真的,真的,萍,你是我的救星,你是天底下顶好的人,你是我——我爱你!(在他身上流泪)
萍 (感动地,用手绢擦着眼泪)凤,以后我们永远在一块儿了,不分开了。
四 (自慰地,在萍的怀里)嗯,我们离开这儿了,不分开了。
萍 (约束自己)好,凤,走以前我们先见一个人。见完他我们就走。
四 一个人?
萍 你哥哥。
四 哥哥?
萍 他找你,他就在饭厅里头。
四 (恐惧地)不,不,你不要见他,他恨你,他会害你的。走吧,我们就走吧。
萍 (安慰地)我已经见过他。我们现在一定要见他一面,(不可挽回地)不然,我们也走不了的。
四 (胆怯)可是,萍,你——
[萍走到饭厅门口,开门。]
萍 (叫)鲁大海!鲁大海!咦,他不在这儿,奇怪,也许从饭厅的门出去了。(望四凤)
四 (走到萍面前,哀告地)萍,不要管他,我们走吧。(拉他向中门走)我们就这样走吧。
[四凤拉萍至中门,中门开,鲁妈与大海进。两点钟内鲁妈的样子像变了一个人。声音因为在雨里叫喊哭号已经暗哑,眼皮失望地向下垂,前额的皱纹很深地刻在面上,过度的刺激使她变成了呆滞,整个激成刻板的痛苦的模型。她的衣服是像已经烘干了一部分,头发还有些湿,鬓角凌乱地贴着湿的头发。她的手在颤,很小心走进来。]
四 (惊慌)妈!(畏缩)
[略顿,鲁妈哀怜地望着四凤。]
鲁 (伸出手向四凤,哀痛地)凤儿,来!
[四凤跑至母亲面前,跪下。]
四 妈!(抱着母亲的膝)
鲁 (抚摸四凤的头顶,痛惜地)孩子,我的可怜的孩子。
四 (泣不成声地)妈,饶了我吧,饶了我吧,我忘了你的话了。
鲁 (扶起四凤)你为什么早不告诉我?
四 (低头)我疼您,妈,我怕,我不愿意有一点叫您不喜欢我,看不起我,我不敢告诉您。
鲁 (沉痛地)这还是你妈太糊涂了,我早该想到的。(酸苦地,忽而)天,这谁又料得到,天底下会有这种事,偏偏又叫我的孩子们遇着呢?哦,你们妈的命太苦,你们的命也太苦了。
大 (冷淡地)妈,我们走吧,四凤先跟我们回去。我已经跟他(指萍)商量好了,他先走,以后他再接四凤。
鲁 (迷惑地)谁说的?谁说的?
大 (冷冷地望着鲁妈)妈,我知道您的意思,自然只有这么办。所以,周家的事我以后也不提了,让他们去吧。
鲁 (迷惑,坐下)什么?让他们去?
萍 (嗫嚅)鲁奶奶,请您相信我,我一定好好地待她,我们现在决定就走。
鲁 (拉着四凤的手,颤抖地)凤,你,你要跟他走!
四 (低头,不得已紧握着鲁妈的手)妈,我只好先离开您了。
鲁 (忍不住)你们不能够在一块儿!
大 (奇怪地)妈,您怎么?
鲁 (站起)不,不成!
四 (着急)妈!
鲁 (不顾她,拉着她的手)我们走吧。(向大海)你出去叫一辆洋车,四凤大概走不动了。我们走,赶快走。
四 (死命地退缩)妈,您不能这样做。
鲁 不,不成!(呆滞地,单调地)走,走。
四 (哀求)妈,您愿意您的女儿急得要死在您的眼前么?
萍 (走向鲁妈前)鲁奶奶,我知道我对不起你。不过我能尽我的力量补我的错,现在事情已经做到这一步,你——
大 妈(不懂地)您这一次,我可不明白了!
鲁 (不得已,严厉地)你先去雇车去!(向四凤)凤儿,你听着,我情愿你没有,我不能叫你跟他在一块儿。走吧!
[大海刚至门口,四凤喊一声。]
四 (喊)啊,妈,妈!(晕倒在母亲怀里)
鲁 (抱着四凤)我的孩子,你——
萍 (急)她晕过去了。
[鲁妈急按着她的前额,低声唤
大 不用去,不要紧,一点凉水就好。她小时就这样。
[萍拿凉水淋在她面上,四凤渐醒,面呈死白色。]
鲁 (拿凉水灌四凤)凤儿,好孩子。你回来,你回来。我的苦命的孩子。
四 (口渐张,眼睁开,喘出一口气)啊,妈!
鲁 (安慰地)孩子,你不要怪妈心狠,妈的苦说不出。
四 (叹出一口气)妈!
鲁 什么?凤儿?
四 我,我不能告诉你,萍!
萍 凤,你好点了没有?
四 萍,我,总是瞒着你;也不肯告诉您(乞怜地望着鲁妈)妈,您——
鲁 什么,孩子,快说。
四 (抽咽)我,我--(放胆)我跟他现在已经有……(大哭)
鲁 (切迫地)怎么,你说你有--(受到打击,不动。)
萍 (拉起四凤的手)四凤!怎么,真的,你——
四 (哭)嗯。
萍 (悲喜交集)什么时候?什么时候?
四 (低头)大概已经三个月。
萍 (快慰地)哦,四凤,你为什么不告诉我,我,我的——
鲁 (低声)天哪!
萍 (走向鲁)鲁奶奶,你无论如何不要再固执哪,都是我错,我求你!(跪下)我求你放了她吧。我敢保我以后对得起她,对得起你。
四 (立起,走到鲁妈面前跪下)妈,您可怜可怜我们,答应我们,让我们走吧。
鲁 (不做声,坐着,发痴)我是做梦。我的女儿,我自己生的女儿,三十年的功夫——哦,天哪,(掩面哭,挥手)你们走吧,我不认得你们。(转过头去)
萍
鲁 (回头,不自主地)不,不能够!
[四凤又跪下。]
四 (哀求)妈,您,您是怎么?我的心定了。不管他是富,是穷,不管他是谁,我是他的了。我心里第一个许了他,我看见的只有他,妈,我现在到了这一步:他到哪儿我也到哪儿;他是什么,我也跟他是什么。妈,您难道不明白,我——
鲁 (指手令她不要向下说,苦痛地)孩子。
大 妈,妹妹既是闹到这样,让她去了也好。
萍 (阴沉地)鲁奶奶,您心里要是一定不放她,我们只好不顺从您的话,自己走了。凤!
四 (摇头)萍!(还望着鲁妈)妈!
鲁 (沉重的悲伤,低声)啊,天知道谁犯了罪,谁造这种孽!他们都是可怜的孩子,不知道自己做的是什么。天哪!如果要罚,也罚在我一个人身上;我一个人有罪,我先走错了一步。(伤心地)如今我明白了,我明白了,事情已经做了的,不必再怨这不公平的天,人犯了一次罪过,第二次也就自地跟着来。(摸着四凤的头)他们是我的干净孩子,他们应当好好地活着,享着福。冤孽是在我心里头,苦也应当我一个人尝。他们快活,谁晓得就是罪过?他们年青,他们自己并没有成心做了什么错。(立起,望着天)今天晚上,是我让他们一块儿走,这罪过我知道,可是罪过我现在替他们犯了;所有的罪孽都是我一个人惹的,我的儿女都是好孩子,心地干净的,那么,天,真有了什么,也就让我一个人担待吧。(回过头)凤儿——
四 (不安地)妈,您心里难过,我不明白您说的什么。
鲁 (回转头。和蔼地)没有什么。(微笑)你起来,凤儿,你们一块儿走吧。
四 (立起,感动地,抱着她的母亲)妈!
萍 去!(看表)不早了,还只有二十五分钟,叫他们把汽车开出,来,走吧。
鲁 (沉静地)不,你们这次走,是在暗地里走,不要惊动旁人。(向大海)大海,你出去叫车去,我要回去,你送他们到车站。
大 嗯。
[大海由中门下。]
鲁 (向四凤哀婉地)过来,我的孩子,让我好好地亲一亲。(四凤过来抱母;鲁妈向萍)你也来,让我也看你一下。(萍至前,低头,鲁望他擦眼泪)好!你们走吧——我要你们两个在未走以前答应我一件事。
萍 您说吧。
鲁 你们不答应,我还是不要四凤走的。
四 妈,您说吧,我答应。
鲁 (看他们两人)你们这次走,最好越走越远,不要回头,今天离开,你们无论生死,永远也不许见我。
四 (难过)妈,那不——
萍 (眼色,低声)她现在很难过,才说这样的话,过后,她就会好了的。
四 嗯,也好,妈,那我们走吧。
[四凤跪下,向鲁妈叩头,四凤落泪,鲁妈竭力忍着。]
鲁 (挥手)走吧!
萍 我们从饭厅出去吧,饭厅里还放着我几件东西。
[三人——萍,四凤,鲁妈——走到饭厅门口,饭厅门开。繁漪走出,三人俱惊视。]
四 (失声)太太!
繁 (沉稳地)咦,你们到哪儿去?外面还打着雷呢!
萍 (向繁漪)怎么你一个人在外面偷听!
繁 嗯,不只我,还有人呢。(向饭厅上)出来呀,你!
[冲由饭厅上,畏缩地。]
四 (惊愕地)二少爷!
冲 (不安地)四凤!
萍 (不高兴,向弟)弟弟,你怎么这样不懂事?
冲 (莫明其妙弟)妈叫我来的,我不知道你们这是干什么。
繁 (冷冷地)现在你就明白了。
萍 (焦躁,向繁漪)你这是干什么?
繁 (嘲弄地)我叫你弟弟来跟你们送行。
萍 (气愤)你真卑——
冲 哥哥!
萍 弟弟,我对不起你!(突向繁漪)不过世界上没有像你这样的母亲!
冲 (迷惑地)妈,这是怎么回事?
繁 你看哪!(向四凤)四凤,你预备上哪儿去?
四 (嗫嚅)我……我……
萍 不要说一句瞎话。告诉他们,挺起胸来告诉他们,说我们预备一块儿走。
冲 (明白)什么,四凤,你预备跟他一块儿走?
四 嗯,二少爷,我,我是——
冲 (半质问地)你为什么早不告诉我?
四 我不是不告诉你;我跟你说过,叫你不要找我,因为我——我已经不是个好女人。
萍 (向四凤)不,你为什么说自己不好?你告诉他们!(指繁漪)告诉他们,说你就要嫁我!
冲 (略惊)四凤,你——
繁 (向冲)现在你明白了。(冲低头)
萍 (突向繁漪,刻毒地)你真没有一点心肝!以为你的儿子会替——会破坏么?弟弟,你说,你现在有什么意思,你说,你预备对我怎么样?说,哥哥都会原谅你。
[繁漪跑到书房门口,喊。]
繁 冲儿,说呀!(半晌,急促)冲儿,你为什么不说话?你为什么抓着四凤问?你为什么不抓着你哥哥说话呀?(又顿,众人俱看冲,冲不语)冲儿你说呀,你怎么,你难道是个死人?哑巴?是个糊涂孩子?你难道见着自己心上喜欢的人叫人抢去,一点儿都不动气么?
冲 (抬头,羊羔似的)不,不,,妈!(又望四凤,低头)只要四凤愿意,我没有一句话可说。
萍 (走到冲面前,拉着他的手)哦,我的好弟弟,我的明白弟弟!
冲 (疑惑地,思考地)不,不,我忽然发现……我觉得……我好像并不是真爱四凤;(渺渺茫茫地)以前——我,我,我——大概是胡闹!
萍 (感激地)不过,弟弟——
冲 (望着萍热烈的神色,退缩地)不,你把她带走吧,只要你好好地待她!
繁 (整个消灭,失望)哦,你呀!(忽然,气愤)你不是我的儿子;你不是我的儿子;你不像我,你——你简直是条死猪!
冲 (受侮地)妈!
萍 (惊)你是怎么回事!
繁 (昏乱地)你真没有点男子气,我要是你,我就打了她,烧了她,杀了她。你真是条糊涂虫,没有一点生气的。你还是父亲养的,你父亲的小绵羊。我看错了你——你不是我的,你不是我的儿子。
萍 (不平地)你是冲弟弟的母亲么?你这样说话。
繁 (痛苦地)萍,你说,你说出来;我不怕,我早已忘了我自己(向冲,半疯狂地)你不要以为我是你的母亲,(高声)你的母亲早死了,早叫你父亲压死了,闷死了。现在我不是你的母亲。她是见着周萍又活了的女人,(不顾一切地)她也是要一个男人真爱她,要真真活着的女人!
冲 (心痛地)哦,妈。
萍 (眼色向冲)她病了。(向繁漪)你跟我上楼去吧!你大概是该歇一歇。
繁 胡说!我没有病,我没有病,我神经上没有一点病。你们不要以为我说胡话。(揩眼泪,哀痛地)我忍了多少年了,我在这个死地方,监狱似的周公馆,陪着一个阎王十八年了,我的心并没有死;你的父亲只叫我生了冲儿,然而我的心,我这个人还是我的。(指萍)就只有他才要了我整个的人,可是他现在不要我,又不要我了。
冲 (痛极)妈,我最爱的妈,您这是怎么回事?
萍 你先不要管她,她在发疯!
繁 (激烈地)不要学你的父亲。没有疯——我这是没有疯!我要你说,我要你告诉他们——这是我最后的一口气!
萍 (狠狠地)你叫我说会什么?我看你上楼睡去吧。
繁 (冷笑)你不要装!你告诉他们,我并不是你的后母。
[大家俱惊,略顿。]
冲 (无可奈何地)妈!
繁 (不顾地)告诉他们,告诉四凤,告诉她!
四 (忍不住)妈呀!(投入鲁妈怀)
萍 (望着弟弟,转向繁漪)你这是何苦!过去的事你何必说呢?叫弟弟一生不快活。
繁 (失了母性,喊着)我没有孩子,我没有丈夫,我没有家,我什么都没有,我只要你说:我——我是你的。
萍 (苦恼)哦,弟弟!你看弟弟可怜的样子,你要是有一点母亲的心——
繁 (报复地)你现在也学会你的父亲了,你这虚伪的东西,你记着,是你才欺骗了你的弟弟,是你欺骗我,是你才欺骗了你的父亲!
萍 (愤怒)你胡说,我没有,我没有欺骗他!父亲是个好人,父亲一生是有道德的,(繁漪冷笑)——(向四凤)不要理她,她疯了,我们走吧。
繁 不用走,大门锁了。你父亲就下来,我派人叫他来的。
鲁 哦,太太!
萍 你这是干什么?
繁 (冷冷地)我要你父亲见见他将来的好媳妇再走。(喊)朴园,朴园……
冲 妈,您不要!
萍 (走到繁漪面前)疯子,你敢再喊!
[繁漪跑到书房门口,喊。]
鲁 (慌)四凤,我们出去。
繁 不,他来了!
[朴园由书房进,大家俱不动,静寂若死。]
朴 (在门口)你叫什么?你还不上楼去睡?
繁 (倨傲地)我请你见见你的好亲戚。
朴 (见鲁妈,四凤在一起,惊)啊,你,你,你们这是做什么?
繁 (拉四凤向朴园)这是你的媳妇,你见见。(指着朴园向四凤)叫他爸爸!(指着鲁妈向朴园)你也认识认识这位老太太。
鲁 太太!
繁 萍,过来!当着你父亲,过来,跟这个妈叩头。
萍 (难堪)爸爸,我,我——
朴 (明白地)怎么——(向鲁妈)侍萍,你到底还是回来了。
繁 (惊)什么?
鲁 (慌)不,不,您弄错了。
朴 (悔恨地)侍萍,我想你也会回来的。
鲁 不,不!(低头)啊!天!
繁 (惊愕地)侍萍?什么,她是侍萍?
朴 嗯。(烦厌地)繁,你不必再故意地问我,她就是萍儿的母亲,三十年前死了的。
繁 天哪!
[半晌。四凤苦闷地叫了一声,看着她的母亲,鲁妈苦痛地低着头。萍脑筋昏乱,迷惑地望着父亲同鲁妈。这时繁漪渐渐移到周冲身边,现在她突然发现一个更悲惨的命运,逐渐地使她同情萍,她觉出自己方才的疯狂,这使她很快地恢复原来平常母亲的情感。她不自主地望着自己的冲儿。]
朴 (沉痛地)萍儿,你过来。你的生母并没有死,她还在世上。
萍 (半狂地)不是她!爸,您告诉我,不是她!
朴 (严厉地)混帐!萍儿,不许胡说。她没有什么好身世,也是你的母亲。
萍 (痛苦万分)哦,爸!
朴 (尊严地)不要以为你跟四凤同母,觉得脸上不好看,你就忘了人伦天性。
四 (向母)哦,妈!(痛苦地)
朴 (沉重地)萍儿,你原谅我。我一生就做错了这一件事。我万没有想到她今天还在,今天找到这儿。我想这只能说是天命。(向鲁妈叹口气)我老了,刚才我叫你走,我很后悔,我预备寄给你两万块钱。现在你既然来了,我想萍儿是个孝顺孩子,他会好好地侍奉你。我对不起你的地方,他会补上的。
萍 (向鲁妈)您——您是我的——
鲁 (不自主地)萍——(回头抽咽)
朴 跪下,萍儿!不要以为自己是在做梦,这是你的生母。
四 (昏乱地)妈,这不会是真的。
鲁 (不语,抽咽)
繁 (转向萍,悔恨地)萍,我,我万想不到是——是这样,萍——
萍 (怪笑,向朴)父亲!(怪笑,向鲁妈)母亲!(看四凤,指她)你——
四 (与萍相视怪笑,忽然忍不住)啊,天!(由中门跑下,萍扑在沙发上,鲁妈死气沉沉地立着。)
繁 (急喊)四凤!四凤!(转向冲)冲儿,她的样子不大对,你赶快出去看她。
[冲由中门下,喊四凤。]
朴 (至萍前)萍儿,这是怎么回事?
萍 (突然)爸,你不该生我!(跑,由饭厅下)。
[远处听见四凤的惨叫声,冲狂呼四凤,过后冲也发出惨叫。]
鲁 四凤,你怎么啦!
(同时叫)
繁 我的孩子,我的冲儿!
[二人同由中门跑出。]
朴 (急走至窗前拉开窗幕,颤声)怎么?怎么?
[仆由中门跑上。]
仆 (喘)老爷!
朴 快说,怎么啦?
仆 (急不成声)四凤……死了……
朴 (急)二少爷呢?
仆 也……也死了。
朴 (颤声)不,不,怎……么?
仆 四凤碰着那条走电的电线。二少爷不知道,赶紧拉了一把,两个人一块儿中电死了。
朴 (几晕)这不会。这,这,这不能够,这不能够!
[朴园与仆人跑下。]
[萍由饭厅出,颜色苍白,但是神气沉静的。他走到那张放着鲁大海的手枪的桌前,抽开抽屉,取出手枪,手微颤,慢慢走进右边书房。外面人声嘈乱,哭声,吵声,混成一片。鲁妈由中门上,脸更呆滞,如石膏人像。老仆人跟在后面,拿着电筒。鲁妈一声不响地立在台中。]
老仆 (安慰地)老太太,您别发呆!这不成,您得哭,您得好好哭一场。
鲁 (无神地)我哭不出来!
老仆 这是天意,没有法子。可是您自己得哭。
鲁 不,我想静一静。(呆立)
[中门大开,许多仆人围着繁漪,繁漪不知是在哭在笑。]
仆 (在外面)进去吧,太太,别看啦。
繁 (为人拥至中门,倚门怪笑)冲儿,你这么张着嘴?你的样子怎么直对我笑?冲儿,你这个糊涂孩子。
朴 (走在中门中,眼泪在面上)繁漪,进来!我的手发木,你也别看了。
老仆 太太,进来吧。人已经叫电火烧焦了,没有法子办了。
繁 (进来,干哭)冲儿,我的好孩子。刚才还是好好的,你怎么会死,你怎么会死得这样惨?(呆立)
朴 (已进来)你要静一静。(擦眼泪)
繁 (狂笑)冲儿,你该死,该死!你有了这样的母亲,你该死。
[外面仆人与鲁大海打架声。]
朴 这是谁?谁在这时候打架。
[老仆下问,立时令一仆人上。]
朴 外面是怎么回事?
仆 今天早上那个鲁大海,他这时又来了,跟我们打架。
朴 叫他进来!
仆 老爷,他连踢带打地伤了我们好几个,他已经从小门跑了。
朴 跑了?
仆 是,老爷。
朴 (略顿,忽然)追他去,跟我追他去。
仆 是,老爷。
[仆人一齐下。屋中只有朴园,鲁妈,繁漪三人。]
朴 (哀伤地)我丢了一个儿子,不能再丢第二个了。(三人都坐下来)
鲁 都去吧!他去了也好,我知道这孩子。他恨你,我知道他不会回来见你的。
朴 (寂静,自己觉得奇怪)年青的反而走到我们前头了,现在就剩下我们这些老——(忽然)萍儿呢?大少爷呢?萍儿,萍儿!(无人应)来人呀!来人!(无人应)你们跟我找呀,我的大儿子呢?
[书房枪声,屋内死一般的静默。]
繁 (忽然)啊!(跑下书房,朴园呆立不动,立时繁漪狂喊跑出)他……他……
朴 他……他……
[朴园与繁漪一同跑下,进书房。鲁妈立起,向书房颤踬了两步,至台中,渐向下倒,跪在地上,如序幕结尾老妇人倒下的样子。]
[舞台渐暗,奏序幕之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