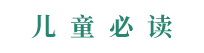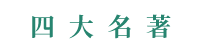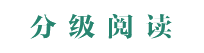第六章
高觉新是觉民弟兄所称为“大哥”的人。他和觉民、觉慧虽然是同一个母亲所生,而且生活在同一个家庭里,可是他们的处境并不相同。觉新在这一房里是长子,在这个大家庭里又是长房的长孙。就因为这个缘故,在他出世的时候,他的命运便决定了。他的相貌清秀,自小就很聪慧,在家里得着双亲的钟爱,在私塾得到先生的赞美。看见他的人都说他日后会有很大的成就,便是他的父母也在暗中庆幸有了这样的一个“宁馨儿”。他在爱的环境中渐渐地长成,到了进中学的年纪。在中学里他是一个成绩优良的学生,四年课程修满毕业的时候又名列第一。他对于化学很感到兴趣,打算毕业以后再到上海或北京的有名的大学里去继续研究,他还想到德国去留学。他的脑子里充满了美丽的幻想。在那个时期中他是一般同学所最羡慕的人。然而恶运来了。在中学肄业的四年中间他失掉了母亲,后来父亲又娶了一个年轻的继母。这个继母还是他的死去的母亲的堂妹。环境似乎改变了一点,至少他失去了一样东西。固然他知道,而且深切地感到母爱是没有什么东西能代替的,不过这还不曾在他的心上留下十分显著的伤痕。因为他还有更重要的东西,这就是他的前程和他的美妙的幻梦。同时他还有一个能够了解他、安慰他的人,那是他的一个表妹。但是有一天他的幻梦终于被打破了,很残酷地打破了。事实是这样:他在师友的赞誉中得到毕业文凭归来后的那天晚上,父亲把他叫到房里去对他说:“你现在中学毕业了。我已经给你看定了一门亲事。你爷爷希望有一个重孙,我也希望早日抱孙。你现在已经到了成家的年纪,我想早日给你接亲,也算了结我一桩心事。我在外面做官好几年,积蓄虽不多,可是个人衣食是不用愁的。我现在身体不大好,想在家休养,要你来帮我料理家事,所以你更少不掉一个内助。李家的亲事我已经准备好了。下个月十三是个好日子,就在那一天下定。今年年内就结婚。”这些话来得太突然了。他把它们都听懂了,却又好像不懂似的。他不作声,只是点着头。他不敢看父亲的眼睛,虽然父亲的眼光依旧是很温和的。他不说一句反抗的话,而且也没有反抗的思想。他只是点头,表示愿意顺从父亲的话。可是后来他回到自己的房里,关上门倒在床上用铺盖蒙着头哭,为了他的破灭了的幻梦而哭。关于李家的亲事,他事前也曾隐约地听见人说过,但是人家不让他知道,他也不好意思打听。而且他不相信这种传言会成为事实。原来他的相貌清秀和聪慧好学曾经使某几个有女儿待嫁的绅士动了心。给他做媒的人常常往来高公馆。后来经他的父亲同继母商量、选择的结果,只有两家姑娘的芳名不曾被淘汰,因为在这两个姑娘之间,父亲不能决定究竟哪一个更适宜做他儿子的配偶,而且两家请来做媒的人的情面又是同样地大。于是父亲只得求助于拈阄的办法,把两个姑娘的姓氏写在两方小红纸片上,把它们揉成两团,拿在手里,走到祖宗的神主面前诚心祷告了一番,然后随意拈起一个来。李家的亲事就这样地决定了。拈阄的结果他一直到这天晚上才知道。是的,他也曾做过才子佳人的好梦,他心目中也曾有过一个中意的姑娘,就是那个能够了解他、安慰他的钱家表妹。有一个时期他甚至梦想他将来的配偶就是她,而且祈祷着一定是她,因为姨表兄妹结婚,在这种绅士家庭中是很寻常的事。他和她的感情又是那么好。然而现在父亲却给他挑选了另一个他不认识的姑娘,并且还决定就在年内结婚,他的升学的希望成了泡影,而他所要娶的又不是他所中意的那个“她”。对于他,这实在是一个大的打击。他的前程断送了。他的美妙的幻梦破灭了。他绝望地痛哭,他关上门,他用铺盖蒙住头痛哭。他不反抗,也想不到反抗。他忍受了。他顺从了父亲的意志,没有怨言。可是在心里他却为着自己痛哭,为着他所爱的少女痛哭。到了订婚的日子他被人玩弄着,像一个傀儡;又被人珍爱着,像一个宝贝。他做人家要他做的事,他没有快乐,也没有悲哀。他做这些事,好像这是他应尽的义务。到了晚上这个把戏做完贺客散去以后,他疲倦地、忘掉一切地熟睡了。从此他丢开了化学,丢开了在学校里所学的一切。他把平日翻看的书籍整齐地放在书橱里,不再去动它们。他整天没有目的地游玩。他打牌,看戏,喝酒,或者听父亲的吩咐去作结婚时候的种种准备。他不大用思想,也不敢多用思想。不到半年,新的配偶果然来了。祖父和父亲为了他的婚礼特别在家里搭了戏台演戏庆祝。结婚仪式并不如他所想象的那样简单。他自己也在演戏,他一连演了三天的戏,才得到了他的配偶。这几天他又像傀儡似地被人玩弄着;像宝贝似地被人珍爱着。他没有快乐,也没有悲哀。他只有疲倦,但是多少还有点兴奋。可是这一次把戏做完贺客散去以后,他却不能够忘掉一切地熟睡了,因为在他的旁边还睡着一个不相识的姑娘。在这个时候他还要做戏。他结婚,祖父有了孙媳,父亲有了媳妇,别的许多人也有了短时间的笑乐,但他自己也并不是一无所得。他得到一个能够体贴他的温柔的姑娘,她的相貌也并不比他那个表妹的差。他满意了,在短时期内他享受了他以前不曾料想到的种种乐趣,在短时期内他忘记了过去的美妙的幻梦,忘记了另一个女郎,忘记了他的前程。他满足了。他陶醉了,陶醉在一个少女的爱情里。他的脸上常常带着笑容,而且整天躲在房里陪伴他的新婚的妻子。周围的人都羡慕他的幸福,他也以为自己是幸福的了。这样地过了一个月,有一天也是在晚上,父亲又把他叫到房里去对他说:“你现在成了家,应该靠自己挣钱过活了,也免得别人说闲话。我把你养到这样大,又给你娶了媳妇,总算尽了我做父亲的责任。以后的事就要完全靠你自己。家里虽然有钱可以送你到下面去继续求学,但是一则你已经有了妻子,二则,现在没有分家,我自己又在管账,不好把你送到下面去。而且你到下面去读书,爷爷也一定不赞成。闲在家里,于你也不好。我已经给你找好了一个位置,就在西蜀实业公司,薪水虽然不多,总够你们两个人零用。你只要好好做事,将来一定有出头的日子。明天你就到公司事务所去办事,我领你去。这个公司的股子我们家里也有好些,我还是一个董事。事务所里面几个同事都是我的朋友,他们会照料你。”父亲一句一句平板地说下去,好像这些话都是极其平常的。他听着,他应着。他并不说他愿意或是不愿意。一个念头在他的脑子里打转:“一切都完了。”他的心里藏着不少的话,可是他一句话也不说。第二天下午,父亲对他谈了一些关于在社会上做事待人应取的态度的话,他一一地记住了。两乘轿子把他们父子送到西蜀实业公司经营的商业场的后门。他跟着父亲走到事务所去,见了那个四十多岁有八字须的驼背的黄经理,那个面貌跟老太婆相似的陈会计,那个瘦长的王收账员,以及其他两三个相貌平常的职员。经理问了他几句话,他都简单地像背书似地回答了。这些人虽然对他很客气,但是他总觉得在谈话上,在举动上,他们跟他不是一类的人,而且他也奇怪为什么以前就很少看见这种人。父亲先走了,留下他在那里,惶恐而孤独,好像被抛弃在荒岛上面。他并没有办事,一个人痴呆地坐在经理室里,看经理跟别人谈话。他这样地坐了整整两个多钟头。经理忽然发见了他,对他客气地说:“今天没有事,世兄请回去罢。”他像囚犯遇赦似的,高兴地雇了轿子回家,一路上催着轿夫快走,他觉得世界上再没有比家更可爱的了。他回到家里,先去见祖父,听了一番训话;然后去见父亲,又是一番训话。最后他回到自己的房里,妻又向他问长问短,到底是从妻那里得到一些安慰。第二天上午十点在家吃过早饭后,他便到公司去,一直到下午四点钟才回家。这一天他有了自己的办公室,而且在经理和同事们的指导下开始做了工作。这样在十九岁的年纪他便大步走进社会了。他逐渐地熟悉了这个环境,学到了新的生活方法,而且逐渐地把他在中学四年中所得到的学识忘掉。这种生活于他不再是陌生的了。他第一次领到三十元现金的薪水的时候,他心里充满着欢喜和悲哀,一方面因为这是自己第一次挣来的钱,另一方面却因为这是卖掉自己前程所得的代价。可是以后一个月一个月平淡地生活下去,他按月领到那三十元的薪水,便再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了,没有欢喜,也没有悲哀。这种生活也还是可以过下去的,没有欢喜,也没有悲哀。虽然每天照例要看见那几张脸,听那些无味的谈话,做那些呆板的事,可是他周围的一切还是平静而安稳。家里的人也不来打扰他,让他和妻安静地过他们的家庭生活。然而不过半年他一生中的另一个大变故又发生了:时疫夺去了父亲,他和弟妹们的哭声并不能够把父亲留住。父亲去了,把这一房的责任放在他的肩上。上面有一个继母,下面有两个在家的妹妹和两个在学校里读书的弟弟。这时候他还只有二十岁。他的心里充满了悲哀,他为死去的父亲而哭,他却不曾想到他自己的处境变得更可悲了。他的悲哀不久便逐渐消去,在父亲的棺木入土以后,他似乎把父亲完全忘记了。他不仅忘记了父亲,同时他还忘记了过去的一切,他甚至忘记了自己的青春。他平静地把这个大家庭的担子放在他的年轻的肩上。在最初的几个月,这个担子还不算沉重,他挑着它并不觉得吃力。可是短短的时期一过,许多有形和无形的箭便开始向他射来,他躲开了一些,但也有一些射到了他的身上。他有了一个新的发现,他看见了这个绅士家庭的另一个面目。在和平的、爱的表面下,他看见了仇恨和斗争,而且他自己也就成了人们攻击的目标。虽然他的环境使他忘记了自己的青春,但是他的心里究竟还燃烧着青春的火。他愤怒,他奋斗,他以为他的行为是正当的。然而奋斗的结果只给他招来了更多的烦恼和更多的敌人。这个大家庭是由四房组织成的。他的祖父本来有五个儿子,但是他的二叔很早就死了。在现有的四房中,除了他自己这一房外,三叔比较跟他接近,四叔和五叔对他不大好,尤其是四婶因为他的继母无意中得罪了她,在暗中跟他这一房闹得厉害,五婶受到四婶的挑拨,也常常跟他的继母作对。由于她们的努力,许多关于他或者他这一房的闲话就流传出去了。他的奋斗毫无结果。而且他也疲倦了。他想,这样不断地跟长辈冲突有什么好处呢?四婶和五婶,再加上一个陈姨太,她们永远是那样的女人。他不能够说服她们,他又何必自寻烦恼,浪费精力呢?于是他又发明了新的处世方法,或者更可以说是处家的方法。他极力避免跟她们冲突,他在可能的范围内极力敷衍她们,他对她们非常恭敬,他陪她们打牌,他替她们买东西。……总之,他牺牲了一部分的时间去讨她们的欢心,只是为了想过几天安静的生活。不久他的大妹淑蓉因肺病死了。这虽然给他带来悲哀,但是他也觉得心里轻松一点,似乎肩上的担子减轻了一些。又过了一些时候,他的第一个婴儿出世了,这是一个男孩。他为了这件事情很感激他的妻,因为儿子的出世给他带来了莫大的欢喜。他觉得自己已经是没有希望的人了,以前的美妙的幻梦永远没有实现的机会了。他活着只是为了挑起肩上的担子;他活着只是为了维持父亲遗留下的这个家庭。然而现在他有了一个儿子,这是他的亲骨血,他所最亲爱的人,他可以好好地教养他,把他的抱负拿来在儿子的身上实现。儿子的幸福就是他自己的幸福。这样想着他得到了一点安慰。他觉得他的牺牲并不是完全白费的。过了两年“五四运动”发生了。报纸上的如火如荼的记载唤醒了他的被忘却了的青春。他和他的两个兄弟一样贪婪地读着本地报纸上转载的北京消息,以及后来上海、南京两地六月初大罢市的新闻。本地报纸上又转载了《新青年》和《每周评论》里的文章。于是他在本城唯一出售新书报的“华洋书报流通处”里买了一本最近出版的《新青年》,又买了两三份《每周评论》。这些刊物里面一个一个的字像火星一样地点燃了他们弟兄的热情。那些新奇的议论和热烈的文句带着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压倒了他们三个人,使他们并不经过长期的思索就信服了。于是《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星期评论》、《少年中国》等等都接连地到了他们的手里。以前出版的和新出版的《新青年》、《新潮》两种杂志,只要能够买到的,他们都买了,甚至《新青年》的前身《青年杂志》也被那个老店员从旧书堆里捡了出来送到他们的手里。每天晚上,他和两个兄弟轮流地读这些书报,连通讯栏也不肯轻易放过。他们有时候还讨论这些书报中所论到的各种问题。他两个兄弟的思想比他的思想进步些。他们常常称他做刘半农的“作揖主义”的拥护者。他自己也常说他喜欢托尔斯泰的“无抵抗主义”。其实他并没有读过托尔斯泰自己关于这方面的文章,只是后来看到一篇《呆子伊凡的故事》。“作揖主义”和“无抵抗主义”对他的确有很大的用处,就是这样的“主义”把《新青年》的理论和他们这个大家庭的现实毫不冲突地结合起来。它给了他以安慰,使他一方面信服新的理论,一方面又顺应着旧的环境生活下去,自己并不觉得矛盾。于是他变成了一个有两重人格的人:在旧社会里,在旧家庭里他是一个暮气十足的少爷;他跟他的两个兄弟在一起的时候他又是一个新青年。这种生活方式当然是他的两个兄弟所不能了解的,因此常常引起他们的责难。但是他也坦然忍受了。他依旧继续阅读新思想的书报,继续过旧式的生活。他看见儿子慢慢地长大起来,从学爬到走路,说简短的话。这个孩子很可爱,很聪明,他差不多把全量的爱倾注在这个孩子的身上,他想:“我所想做而不能做到的,应当由他来替我完成。”他因为爱孩子,不愿意雇奶妈来喂奶,要他的妻自己抚养孩子,好在妻的奶汁也很够。这样的事在这个绅士家庭里似乎也是一个创举,因此又引起外人的种种闲话。但是他都忍受了,他相信自己是为了孩子的幸福才这样做的,而且妻也体会到他这种心思,也满意他这个办法。每天晚上,总是妻带着孩子先睡,他睡得较迟。他临睡时总要去望那个躺在妻的身边、或者睡在妻的手腕里的孩子的天真的睡脸。这面容使他忘记了自己的一切,他只感到无限的爱,他忍不住俯下头去吻那张美丽的小脸,口里喃喃地说了几句含糊的话。这些话并没有什么意义,它们是自然地从他的口中吐出来的,那么自然,就像喷泉从水管里喷出来一样。它们只是感激、希望与爱的表示。他并不知道从前他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他也曾经从父母那里受到这样的爱,他也曾经从父母那里听到这样的充满了感激、希望与爱的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