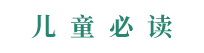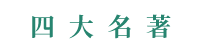第三章 白雀(一):二
晚上
桑桑在花园里循声捉蟋蟀
就听见荷塘边的草地上有笛子声
隔水看
白雀正在笛子声里做动作。今晚的月亮不耀眼
一副迷离恍惚的神气。桑桑看不清蒋一轮与白雀
但又分明看得清他们的影子。蒋一轮倚在柳树上
用的是让桑桑最着迷的姿势:两腿微微交叉着。白雀的动作在这样的月光笼罩下
显得格外的柔和。桑桑坐在塘边
呆呆地看着
捉住的几只蟋蟀从盒子里趁机逃跑了。
微风翻卷着荷叶
又把清香吹得四处飘散。几支尚未绽开的荷花立在月色下像几支硕大的毛笔
黑黑地竖着。桑桑能够感觉到:它们正在一点一点地开放。
夜色下的笛子声不太像白天的笛子声
少了许多明亮和活跃
却多了些忧伤与神秘。夜越深越是这样。
路过塘边的人
都要站住听一会
看一会。听一会
看一会
又走了。但桑桑却总在听
总在看。桑桑在想:有什么样的戏
只是在月光下演呢?
不知是哪个促狭鬼
向池塘里投掷了一块土疙瘩
发一声“咚”的水响
把蒋一轮的笛音惊住了
把白雀的动作也惊住了。
桑桑在心里朝那个投掷土疙瘩的人骂了一声:“讨厌!”但笛音又响起来了
动作也重新开始。如梦如幻。
过了一个星期
彩排结束后
桑乔说:“《红菱船》怕是今年最好的一出戏了。”
演出是在一个晴朗无风的夜晚。演出的消息几天前就已传出去了
来看演出的人很多。舞台就设在油麻地小学的操场上。在通往油麻地小学操场的各条路上
天未黑
人便一缕一缕地往这边走了。老头老太太
大多扛了张板凳
而孩子们心想:操场四周都是树
到时爬树上看吧。因此
他们大多就空了手
轻松地跑着
跳着
叫着。油麻地小学文艺宣传队与油麻地地方文艺队的演出水平
是这一带最好的
因此
来看演出的绝非仅仅只有油麻地的人
差不多
引来了方圆十里地的人。油麻地一些人家估计一些住在远处的亲戚也要过来
就多扛了一些凳子。因此
离演出还早
场地上就已放了无数张凳子了
看上去挺壮观。
化妆室就设在用做排练场的那幢草房子里。来得早的人
就围在窗口门口看化妆。桑乔手掌上涂满了各色油彩。演员们就从他手下
一个个地过着。若是个过场的或不重要的
桑乔就三下两下地将他们打发过去。若是一个重要角色
桑乔就很认真
妆化得差不多了
就让那个演员往后退几步
他歪头看看
叫演员凑上来
让他再作仔细修改
就像一个作文章的人
仔细地修改他的文章一样。
乐队在门外已开始调音、试奏。
桑乔化妆着化妆着
心里老觉得今天好像有点什么事情
偶尔抬头看了一眼
一下看到了心神不宁的蒋一轮
他突然明白了:白雀还没化妆呢。他问道:“白雀呢?”
“白雀还没有来。”有人一旁答道。
桑乔在嘴里嘀咕了一声:“怎么搞的?该来了。”心想离演出还有些时间
就依然去给那些演员化妆。
蒋一轮屋里屋外不安地转悠已经好一会了
看看手表
离演出时间已不远了
终于走到桑乔身边
轻声说道:“桑校长
她还没有来。”
桑乔无心再去仔细化妆手里的一个演员
说声“行了”
就丢下那个演员
对一个叫‘泣酸子”的演员说:“二酸子
你去她家找找她。”
二酸子上路了。
桑乔追出来:“快点。”
“唉!”二酸子穿过人群跑起来。
演员、乐队以及围观的人
不一会就都知道了白雀未到
就把一句话互相重复着:“白雀还没有来呢。”又过不一会
这话就传到了操场上
认识不认识的都在说:“白雀还没有来呢。”觉得事情似乎挺重大
于是也就感到有点莫名其妙的兴奋。
二酸子过不一会回来了
对桑乔说:“白雀他父亲不让她来。”
桑乔问:“为什么?”
二酸子不知为什么看了蒋一轮一眼
转而回答桑乔:“不知道为什么。”
还有两三个演员没化妆
桑乔说:“自己化妆吧。”又对宣传队的具体负责人说:唯时演出
我去白雀家一趟。”说完就走
一句话一半留在门里
一半留在门外:“谁都可以不来
但白雀不能不来。”
两盏汽油灯打足了气
“璞璞璞”地燃烧着
一旦高悬
立即将舞台照得一片光明。
演出准时进行。但台下的人一边看演出
一边就在下面互相问:“白雀来了吗?”台后的演员也在互相问:“白雀来了吗?”
桑桑看到蒋一轮在吹笛子时
不时拿眼睛往通往操场的路上膘。好几回
蒋一轮差一点把曲子吹错了
幸亏是合奏
很用心的桑桑用胡琴将这些小漏洞一一补住了。桑桑看到
蒋一轮用感激和夸奖的目光看了他好几回。
幕间
人们在空隙里几乎将询问变成了追问:“白雀来了没有?”
又一个节目开始时
人们的注意力就集中不起来
场上的秩序不太好。
演员们开始抱怨白雀:“这个白雀
搞得演出要演不下去了。”
演了三个小节目
白雀还未到。人们从“白雀偶然疏忽了
忘了演出时间了”的一般想法上移开去
在问:“白雀为什么没有来?”都认为是有原因的
便开始了猜测
心思就老不在台上演出的节目上。仿佛他们今天来这里
不是来看演出的
而是来专门研究“白雀为什么没有来”这样一个问题的。当他们听说白雀是被她的父亲白三拦在了家中时
猜测就变得既漫无边际
又十分具体了。台下一片卿卿喳喳
想看节目的人也听不太分明了
注意力反而被那些有趣的猜测吸引了。因此
这时台上的演出
实际上已没有太大的意义
台前台后的演员都很着急:“白雀怎么还不来呢?”
忽然有人大声说:“白雀来了!”
先是孩子们差不多一起喊起来:‘噢——白雀来了——”大人们看也不看
就跟着喊。
众人都去望路上
台上的演员和乐队也都停住了望路上——月光下的路
空空荡荡。
“哪儿有白雀?”“没有白雀。”“谁胡说的?”一场的人
去哪儿找那个胡说的人!众人只当穿插进来了一个节目
这个节目让他们觉到了一阵小小的冲动。
台上的演出继续进行。台下的人暂时先不去想白雀
勉勉强强地看着
倒有了一阵好秩序。演员们也就情绪高涨。那个男演员
亮开喉咙大声吼
吼得人心一阵激动。本是风吹得树叶响
但人却以为是那个男演员的声音震得树叶“沙沙”响。桑桑把胡琴拉得摇头晃脑
揉弦揉走了音。只有蒋一轮
还是心不在焉
笛子吹得结结巴巴
大失往日的风采。人也没有从前一吹笛子就一副得意忘形的样子
显得有点僵硬。
一个女演员做着花样
一摇一晃
风吹杨柳似地走上台来。她一直走到了台口
让人觉得她马上就要走下台来了。下面一个动作
是她远眺大河上有一叶白帆飘过来。她身子向前微侧
突然说出一句:“那不是白雀吗?”神情就像说的是戏里头的一句台词。
众人起先反应不过来
还盯着她的脸看。
她踞起脚
用手往路上一指:“白雀!”
众人立即站起来
扭头往路上看
只见路上袅袅娜娜地走过来一个年轻女子。
“是白雀!”
“就是白雀!”
众人就看着白雀不慌不忙地走过来。
白雀并不着急。人们隐隐约约地看到
她一路走
还一路不时地伸手抓一下路边的柳枝或蹲下来采支花什么的。人们不生气
倒觉得白雀也真是不一般。
靠近路口
不知是谁疑惑地说了一声:“是白雀吗?”
很多人跟着怀疑:“是白雀吗?”
话立即传过来:“是周家的二丫!”
于是众人大笑。因为周家的二丫
是个脑子有毛病的姑娘
一个“二百五”。
二丫走近了
明亮的灯光下
众人清清楚楚地看清了是二丫。
二丫见那么多人朝她笑
很不好意思
又袅袅娜娜地走进了黑暗的树荫里。
台上那个女演员满脸通红
低下头往后台走。再重上台来时
就一直不大好意思
动作做没做到家
唱也没唱到家
勉强对付着。
台下有人忽然学她刚才的腔调:“那不是白雀吗?”
众人大笑。
女演员没唱完
羞得赶紧往后台跑
再也没有肯上台。
台下的秩序从此变得更加糟不可言。很多人不想演了。桑桑和其它孩子、大人、乐手坐在台上很尴尬
不知道是撤下台来还是坚持着在台上。
台下的人很奇怪:非想见到白雀不可。其实
他们中间的大部分人
并不认识白雀
更谈不上对白雀演戏的了解。只是无缘无故地觉得
一个叫白雀的演员没有来
不是件寻常的事情。而互相越是说着白雀
就越觉得今天他们之所以来看戏
实际上就是来看白雀的
而看不到白雀
也就等于没有看到戏。这种情绪慢慢地演变成了对演出单位的恼火:让我们来看戏
而你们的白雀又没有来
这不是讴人么?这不是让我们白跑一趟吗?又等了等
终于有了想闹点事的心思。
演员们说:“不要再演了。”
宣传队的负责人说:“桑校长没回来。演不演
要得到他的同意。”
“桑校长怎么到现在还不回来呢?”有几个演员走到路口去望
但没有望见桑乔。
台下终于有人叫:“我们要看白雀!”
很多人跟着喊:“我们要看白雀!”
这时演员们即使想演
实际上也很难演下去了。
演员与乐队都撤到了后台。
台下乱哄哄的像个集市。
蒋一轮站在一棵梧桐树的黑影里
一脸沮丧。
桑乔终于回来。演员们连忙将他围住
就听他说了一声:“我真想将白三这厮一脚瑞进大粪坑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