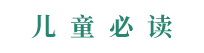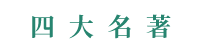第87节
正在小羊圈里的日本男女围绕着大槐树跳跃欢呼的时节,有一条小小的生命来给程长顺接续香烟。他,那小小的新生命,仿佛知道自己是亡国奴似的,一降生就哇哇的哭起来。
程长顺象喝醉了似的,不知道了东西南北。恍惚的他似乎听到了珍珠港被炸的消息,恍惚的他似乎看见了街上的日本醉鬼。可是,那都只是恍惚的,并没给他什么清楚的印象。他忙着去请收生婆,忙着去买草纸与别的能买到的,必需的,小东西。出来进去,出来进去,他觉得他自己,跟日本人一样,也有点发疯。
他极愿意明白珍珠港是什么,和它与战局的关系,可是他更不放心他的老婆。这时候,他觉得他的老婆比世界上任何人都更重要,生小孩比世界上任何事情都更有价值;好象世界战争的价值也抵不过生一个娃娃。
马老寡妇也失去平日的镇静,不是为了珍珠港,而是为了外孙媳妇与重孙的安全。她把几年来在日本人手下所受的苦痛都忘掉,而开始觉出自己的真正价值与重要。是她,把长顺拉扯大了的;是她,给长顺娶了老婆;是她,将要变成曾祖母。她的地位将要和祁老人一边儿高,也有了重孙!
她高兴,又不放心;她要镇定,而又慌张;她不喜多说多道,而言语会冲口而出。她的白发披散开,黄净子脸上红起来一两块。她才不管什么珍珠港不珍珠港,而只注意她将有个重孙;这个娃娃一笑便教中国与全世界都有了喜气与吉利。
小羊圈里的人们听到这吉利的消息,马上都把战争放在一边,而把耳目放在程家的事情上。至少,这将要降生的娃娃已和全世界的兵火厮杀相平衡了;战争自管战争,生娃娃到底还是生娃娃;生娃娃永远,永远,不是坏事!他们都等待着娃娃的哭声,好给马老太太与程长顺道喜。是的,他们必须等着道喜;他们觉得在这时候生娃娃是勇敢的,他们不能不佩服程长顺与小程太太。
李四大妈的慌忙,热烈,又比马老太太的大着好几倍。产房的事她都在行,她不能不去作先锋。生娃娃又是给她增多“小宝贝”的事,她的热心与关切理应不减于产妇自己的,假若不是更多一点。在万忙之中,她似乎听到一声半声的珍珠港。她挤咕着近视眼告诉大家:“好,你们杀人吧,我们会生娃娃!”
小程太太什么也不知道,不知道珍珠港,不知道世界在血泪里将变成什么样子。她甚至于顾不得想起小崔,与杀死小崔的日本人。她只知道自己身上的疼痛,和在疼痛稍停时的一种最实际的希望——生个娃娃。她忘了一切,而只记得人类一切的根源,生孩子!
娃娃生下来了,是个男的。全世界的炮火声并没能压下去他的啼哭。这委屈的,尖锐的,脆弱而伟大的啼声,使小羊圈的人们都感到兴奋,倒好象他们都在黑暗中看见了什么光明与希望。
及至把这一阵欢喜发泄在语言与祝贺中之后,他们才想到,他们并拿不出任何东西去使道喜的举动更具体化一点,象送给产妇一些鸡蛋,黑糖,与小米什么的。孩子是小程太太生的,而鸡蛋,糖,与小米,都在日本人手里拿着呢。
由这个,他们自然而然的想到:生娃娃,在这年月,不是喜事,而是增加吃共和面的小累赘。这小东西或者不会长成健壮的孩子,因为生下来便吃由共和面变成的乳,假若共和面也会变成乳的话。这样,由生,他们马上看到夭折。生与死是离得那么近,人生的两极端可以在一个婴儿身上看到。他们没法再继续的高兴了。
孩子生下来的第二天,英美一齐向日本宣战。程长顺本想给那个满脸皱纹的娃娃起个名子,可是他安不下心去。看一眼娃娃,他觉得自己有了身分。可是,一想到全世界的战争,他又觉得自己毫无出息——在这么大的战争里,他并没尽丝毫的力气。他只是由没出息的人,变成没出息的父亲。看,那个红红的,没有什么眉毛的,小皱脸!那便是他的儿子,卷着一身的破布——都是他由各处买来的破烂。他的儿子连一块新布都穿不上!他不敢再看那个寒伧的小东西。
小儿的三天,中国对德意与日本宣战。程长顺,用尽他的知识与思想,也不明白为什么中国到今天才对日本宣战。可是,明白也罢,不明白也罢,他觉得宣战是对的。宣战以后,他想,一切便黑是黑,白是白,不再那么灰渌渌的了。而且,他也想到,今天中国对日宣战,想必是中国有了胜利的把握。哈,他的儿子必是有福气的。想想看,假若再打一年半载,中国就能打胜,他的儿子岂不是就自幼儿成为太平时代的人?儿子,哼,不那么抽抽疤疤的难看了。细看,小孩子也有眉毛啊!是的,这个娃娃的名子应当叫“凯”。他不由的叫了出来:“凯!凯!”娃娃居然睁了睁眼!
可是,凯的三天过得并不火炽。邻居们都想过来道喜,可是谁也拿不出贺礼,也就不便空着手过来。马老太太本想预备点喜酒,招待客人。可是,即使她有现成的钱,她也买不到东西。战争是不轻易饶恕任何人的,小凯的三天只好鸦雀无声的过去吧。
只有李四妈不知由哪里弄来五个鸡蛋,用块脏得出奇的毛巾兜着,亲自送了来。把五个蛋交出去,她把多年积下的脏野的字汇全搬出来,骂她自己,“那个老东西”,与日本人,因为她活了一世,向来没有用过五个鸡蛋给人家贺喜。“五个蛋,丢透了人喽!”她拍打着自己的大腿,高声的声明。
可是,马老太太被感动得几乎落了泪。五个鸡蛋,在这年月,上哪儿找去呢!
祁家的老人,早已听到程家的喜信儿,急得不住的叹气。他是这胡同里的老人星,他必须到程家去贺喜,一来表示邻居们的情义,二来好听人家说:“小娃娃沾你老人家的光,也会长命百岁呀!”可是,他不能去,没有礼物呀。
天佑太太,听到老人的叹气,赶紧到处搜寻可以当作礼物的东西。从掸瓶底儿上,她找出一个“道光”的大铜钱来。把大铜钱擦亮,她又找了几根红线,拴巴拴巴,交给了妞妞,教妞妞去对老人说:“把这个给程家送去好不好?”
老人点了头。带着重孙子,重孙女,他到程家去证实自己是老人星。
祁老人带着孩子们走后,瑞宣在街门外立了一会儿。他刚要转身回去,一位和尚轻轻的走过来,道了声“弥陀佛”。瑞宣立定。和尚看左右无人,从肥大的袖口中掏出一张小纸,递给了瑞宣;然后又打了个问讯,转身走去。
瑞宣赶紧走进院内,转过了影壁才敢看手中的纸条。一眼,他看明白纸条上的字是老三瑞全的笔迹。他的心跳得那么快,看了三遍,他才认明白那些字:“下午二时,中山公园后门见面,千万!”
握着纸条,他跑进屋中,一下子躺在了床上。他好象已不能再立住了。躺在床上,第一个来到心中的念头是:“我叫老三逃出去的!”这使他得意,自傲。
他想:老三必定在外面作过了惊天动地的事,所以才被派到北平来作最危险的工作。哈,他教老三逃出去的,老三的成功也间接的应当是他自己的成功!好,无论怎么说吧,有这么一个弟弟就够了,就够给老大老二赎罪的了。过了一会儿,他不那么高兴了。假若老三问他:“父亲呢?老二呢?”他怎么回答?老三逃出去是为报国,他自己留在家里是为尽孝。可是,他的孝道在哪儿呢?他既没保住父亲的命,也没能给父亲报仇!他出了汗,他没脸去见老三!
不,老三也许不会太苛责他。老三是明白人,而且在外面闯练了这么几年。对的,老三必定会原谅大哥的。瑞宣惨笑了一下。
他想去告诉韵梅:“你说对了,老三确是回来了!”他也想去告诉母亲,祖父,和邻居们:“我们祁家的英雄回来了!”可是,他没有动。他必须替自家的英雄严守秘密。这个,使他难过,又使他高兴——哈,只有他自己知道老三回来,他是英雄的哥哥!
他怀疑自己的破表是不是已经停住。为什么才是十一点钟呢?他开开屋门,看看日影;表并没有停住,影子告诉他,还没到正午。
他不知道怎么吞下去的一点午饭,不知怎么迷迷糊糊的走出街门。走了半天,他才明白过来,时间还太早。虽然明白过来,他可是依然走得很快。他好象已管束不住自己的脚。是的,他是去看他的弟弟,与中国的英雄。
哼,老三必定象一个金盔金甲的天神,那么尊严威武!
天气相当的冷,可是没有风,冷得干松痛快。穷破的北平借着阳光,至少是在瑞宣心里,显出一种穷而骄傲的神色。
远远的,他看见了禁城的红墙,与七十二条脊的黄瓦角楼。他收住脚步,看了看表,才一点钟。他决定先进到公园里去,万一瑞全能早来一些呢。
公园里没有什么游人。御河沿上已没有了茶座,地上有不少发香的松花。他往南走。有几个青年男女在小溜冰场上溜冰。他没敢看他们。不管他们是汉奸的,还是别人的,子弟,反正他们都正和老三相反:不知道去抗敌,而在这里苟安,享受。他不屑于看他们。
他找了松树旁的一条长凳,坐下。阳光射在他的头上,使他微微的发倦。他急忙立起来,他必不可因为困倦而打盹儿,以至误了会见老三的时间。
好容易到了两点钟,他向公园后门走去。还没走到,迎面来了个青年,穿着件扯天扯地的长棉袍。他没想到那能是老三。
老三扑过大哥来。“哈,不期而遇!瑞大哥!”老三的声音很高,似乎是为教全公园的人都能听到。
瑞宣这才看明白了老三。他的眼泪要夺眶而出。可是瑞全没给大哥留落泪的机会。一手扯着大哥的臂,他大声的说:“来,再溜一趟吧!老哥儿俩老没见了,大嫂倒好?”瑞宣晓得老三是在作戏,也知道老三必须作戏,可是,他几乎有点要恨老三能这么控制住感情去作戏。
瑞宣愿意细看看老三,由老三的脸看到老三的心。可是,老三扯着他一劲往前走。
瑞宣试着找老三的脸,老三的脸可是故意的向一旁扭着点。这,教瑞宣明白过来:老三是故意把脸躲开,因为弟兄若面对了面,连老三也恐怕要落泪的。他不恨老三了。老三不但有胆子,也知道怎么小心。真的,老三并不象金盔金甲的天神;可是老三的光阴并没白白的扔弃,老三学会了本事。老三已不是祁家四世同堂的一环,而是独当一面的一个新中国人。看老三那件扯天扯地的棉袍!
“我们坐一坐吧?”瑞宣好容易想起这么句话来。兄弟坐在了一棵老柏的下面。
瑞宣想把四年来的积郁全一下子倾吐出来。老三是他的亲弟弟,也是最知心的好友。他的委屈,羞愧,都只能向老三坦白的述说;而且,他也知道,只能由老三得到原谅与安慰。
可是,他说不出话来。身旁的老三,他觉得,已不是他的弟弟,而是一种象征着什么的力量。那个力量似乎是不属于瑞宣的时代,国家的。那个力量,象光似的,今天发射,而也许在明天,明年,或下一世纪,方能教什么地方得到光明。他没法对这样的一种力,一种光,诉说他自己心中的委屈,正象萤火不敢在阳光下飞动那样。这样,他觉得老三忽然变成个他所不认识的人。他本极想细看看弟弟,现在,他居然低下头去了;离着光源近的感到光的可怕。
老三说了话:“大哥,你怎么办呢?”
“嗯?”瑞宣似乎没听明白。
“我说,你怎么办呢?你失了业,不是吗?”
“啊!对!”瑞宣连连的点头。在他心里,他以为老三不开口则已,一开口必定首先问到祖父与家人。可是,他没想到老三却张口就问他的失业。呕,他一定不要因此而恼了老三,老三是另一世界的人,因此,他又“啊”了一声。“大哥!”瑞全放低了声音:“我不能在这里久坐!快告诉我,你教书去好不好?”
“上哪儿去教书?”瑞宣以为老三是教他到北平外边去教书。他愿意去。一旦他离开北平,他想,他自己便离老三的世界更近了一点。
“在这里!”
“在这里?”瑞宣想起来一片话:“这四年里,我受了多少苦,完全为不食周粟!积极的,我没作出任何事来;消极的,我可是保持住了个人的清白!到现在,我去教书,在北平教书,不论我的理由多么充足,心地多么清白,别人也不会原谅我,教我一辈子也洗刷不清自己。赶到胜利的那一天来到,老朋友们由外面回来,我有什么脸再见他们呢?我,我就变成了一个黑人!”瑞宣的话说得很流畅了。他没想到,一见到老三,他便这样象拌嘴似的,不客气的,辩论。同时,他可是觉得他应当这么不客气,不仅因为老三是他的弟弟,而且也因为老三是另一种人,他须对老三直言无隐。他感到痛快。“教我去教书也行,除非……”
“除非怎样?”
“除非你给我个证明文件,证明我的工作是工作,不是附逆投降!”
老三楞了一会儿才说:“我没有给任何人证明文件的权,大哥!”没等大哥回话,他赶紧往下说:“我得告诉你,大哥:当教员,当我所要的教员,可就是跟我合作,有危险!哪个学校都三天两头的有被捕的学生和教员。因此,我才需要明知冒险而还敢给学生们打气的教员。日本人要用恐怖打碎青年们的爱国心,我们得设法打碎日本人的恐怖。一点不错,大哥,你应当顾到你的清白;可是,假若你到了学校,不久就因为你的言语行动而被捕,不是也没有人知道吗?在战争里,有无名的汉奸(象贪官污吏和奸商),也有无名的英雄。你说你怕不明不白的去当教员,以后没脸见人;可是你也怕人不知鬼不觉的作个无名英雄吗?我看哪,大哥,我明白你,你自己明白你,就够了,用不着多考虑别的。”
瑞宣没敢说什么。
“还有,大哥,太平洋上的战争开始,我也许得多往乡下跑,去探听军事消息。我所担任的宣传工作,顶好由钱伯伯负责。我不能把那个责任交给你,因为太危险;可是你至少可以帮助钱伯伯一点,给他写点文章。假若你到学校里去,跟青年们接近,你自然可以得到写作的资料。你看怎样?大哥!”瑞宣的脑子里象舞台上开了幕,有了灯光,鲜明的布景,与演员。他自己也是演员之一。他找到了自己在战争的地位。
啊,老三并没有看不起他的意思。老三教他去冒险,去保护学生,去写文章!好吧,既是老三要求他去这么作,他便和老三成为一体;假若老三是个英雄,自己至少也会是半个,或四分之一的英雄!
老三始终没提到家中的问题;老三对啦!要顾家,就顾不了国。是的,他不必再问:“假若我去危险,我被捕,家中怎办呢?”不必问,不必问。那问题或者只教老三为难,使自己显出懦弱。老三是另一种人,只看大处,不管小节目。他,瑞宣,应当跟老三学。况且,自己就是不去冒险,家中不也是要全饿死吗?他心中一亮,脸上浮出笑容:“老三,我都听你的就是了!你说怎办就怎办!”
说完,看着老三。他以为老三必定会兴奋,会夸赞他。可是,老三没有任何表示,而只匆匆的立起来:“好,听我的信儿吧!我不敢在这儿坐久了,我得走!我出前门儿,不用跟着我!再见,大哥!”老三向公园前面走去。
瑞宣仍在那儿坐着,眼看着老三的背影,他心中感到空虚;哼,老三没有任何表示!
过了一会儿,他惨笑了一下,立起来。“老三变了,变得大了!哼,瑞宣,你又不是个小孩子,还需要老三说几句好听的话鼓励你?老三是真杀真砍的人,他没工夫顾到那些婆婆妈妈的小过节呀!”
他又向公园前门儿打了一眼。老三已经不见了。“就是这样吧!”他告诉自己:“说不定,我会跟老三一样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