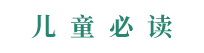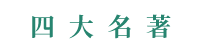第一章 玛妮娅
诺佛立普基路上那座中学教学楼里,每逢星期天都是静悄悄的。
楼门上方的三角形石门额上,刻着“男子高中”几个俄文字。最宽的大门上了闩,柱廊的模样看上去像座废弃的庙宇。这是一座结构长而低矮的平房,此时杳无人迹,阳光明亮的教室里,摆着一排排黑色课桌,上面用铅笔刀刻着名字的缩写。周围非常寂静,只能听见圣母教堂的钟声在召唤人们去做晚祷,街上不时传来货运马车的辚辚车轮声,时而能听到拉着四轮马车的懒洋洋拉车马踏出的嘚嘚声。篱笆包围的院子里有四棵紫丁香开了花,虽然枝叶稀疏,树叶上还遮盖着一层灰土,但是街上身穿星期日盛装的人们仍然为芬芳的花香所吸引,禁不住扭过头来,露出一脸惊喜。在华沙,严霜刚刚褪去,立刻毒日炎炎。五月未尽,天气已经很热了。
安息日的平静被打破了。教学楼左翼一层传来一阵奇怪的声音,还伴随着沉闷的回音,物理教师兼副督学伏拉迪斯拉夫·斯科洛多斯基先生就住在这里。那声音就像铁锤在胡乱敲打。接着是一阵坍塌的轰响,夹杂着尖利的嘶喊声,敲打声在继续。几个声音操着波兰语大声嚷着:
“海拉,我的弹药用光了!”
“塔楼,约瑟夫!瞄准塔楼!”
“玛妮娅,躲开!”
“干吗躲开?我给你送积木来啦!”
“哎呀!呀!”
光滑的地板上,随着一阵崩溃的声音,积木塔楼轰然坍塌。一时尖叫声四起,积木块乱飞起来,散落在四处。
战场是一个宽敞的方屋子,几扇窗户朝向后院的体育活动室。屋子里摆放着四张童床,四个孩子正在大喊大叫,玩打仗游戏,他们最小的五岁,最大的九岁。斯科洛多斯基家这四个孩子当成弹药的积木是叔叔送给他们的圣诞节礼物,叔叔性情平和耐心,喜欢打惠斯特牌,绝对没料到他送的礼物竟落得如此下场。有那么几天,约瑟夫、布罗妮娅、海拉和玛妮娅顺从大人愿望,仔细按照大木箱里附带的示范图,用积木搭建城堡、小桥、教堂等。但是,积木很快便有了实在的用途:短小的橡木柱子当作大炮,小方木块就是炮弹,年轻的建筑师们摇身一变,成了一个个陆军元帅。
约瑟夫趴在地板上匍匐前进,有章有法地把大炮对准敌人。孩子的一头金发下,脸蛋儿健康红润,尽管在酣战中也露出军队指挥官一般的坚毅神色。四个孩子中,他年龄最大,学过的本事最多,他还是唯一的男孩。他周围全是女孩子,几个女孩儿身穿铜样的衣服,都是星期日才穿的好衣服,小衣领上有褶皱,深色围裙上缀着花边。
说句公道话,姑娘们作战也很勇敢。海拉是约瑟夫的同盟,她两眼炯炯有神,飒爽英姿。海拉只有六岁半,心里真希望自己是个大孩子,她想把积木块抛得远远的。海拉嫉妒布罗妮娅,因为姐姐已经八岁了。布罗妮娅是个脸上长着酒窝的漂亮女孩,她扑上前去保卫两扇窗户之间的部队时,一头金发飘荡起来。
布罗妮娅这一边有她的副官,这位小姑娘用漂亮的小围裙兜着弹药,在一个个军营中间来回奔跑忙乱,一边高声喊杀,放声大笑,两个小脸蛋涨得通红。
“玛妮娅!”
小姑娘奔跑中突然止步,抓围裙的手顿时放开,一兜积木飞撒出去。
“怎么啦?”
喊她的是刚刚走进屋子的苏西娅。苏西娅是五个孩子中年龄最大的,虽然年龄还不到十二岁,可是在小弟弟和小妹妹面前却俨然是个大人了。她一头沙黄色头发披散在肩膀上,漂亮的面孔露出洋溢的热情,一双清澈的灰眼睛显得煞有介事。
“妈妈说你已经玩得太久,别玩了。”
“可布罗妮娅需要我……我得给她送积木!”
“妈妈说叫你现在就去。”
玛妮娅迟疑片刻,然后拉着姐姐的手,神色庄重地退出战斗。五岁的孩子玩打仗太吃力,小姑娘几乎把力气用尽了,退出战斗也没有多少不情愿。隔壁传来一个声音,温和得像是在爱抚她:“玛妮娅……玛妮西娅……我的小宝贝安秀佩西奥……”
在波兰,人们特别喜欢用昵称。斯科洛多斯卡家叫大女儿从来不用苏菲,总是叫“苏西娅”,把布罗妮施拉娃叫成“布罗妮娅”,海伦成了“海拉”,约瑟夫成了“约西奥”。最小的女儿玛丽亚昵称最多,她毕竟是家里最受宠爱的孩子嘛。“玛妮娅”是常用的昵称,“玛妮西娅”是个爱称,而“安秀佩西奥”这个逗乐的爱称从婴儿时期就开始叫了。
“我的安秀佩西奥,看你头发乱成啥样子了!看两个小脸蛋红的!”
一双苍白干瘦却灵巧的手把她围裙下面的带子系好,捋顺那头短短的卷发,露出一张倔犟的面孔,孩子的紧张神色渐渐松弛下来。这就是我们那位未来的科学家。
玛妮娅跟妈妈最亲。在她眼里,世界上谁也没有妈妈这么温和善良,而且谁也没有她这么聪明。
斯科洛多斯卡夫人出生在一个乡村绅士家庭,在家里是长女,父亲菲利克斯·博古斯基家有不多的一些田产,在波兰,这一阶层人数众多。由于靠自家田地度日太清苦,他便替稍富些的人家管理田地。他的婚姻相当浪漫:他与一个没有财产的贵族小姐相爱,便不顾美女家父母反对,两人私奔成婚。随着岁月流逝,原来那个诱拐贵族小姐的人已经变成个颤巍巍的胆小老人,他倾心的女子也成了脾气暴躁的老祖母。
他们的六个孩子中,斯科洛多斯卡夫人无疑是性情最平和、头脑最聪明的。她在华沙一所私立学校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便决定献身教育事业,就在母校留校任教,后来当了这所学校的校长。一八六〇年,一位名叫弗拉迪斯拉夫·斯科洛多斯基的教师向这位才貌双全的女子求婚。虽然她没钱,却出身世家,虔诚尽责,行动积极,终生职业无虞。另外,她还是个音乐家,会弹钢琴会唱歌,软绵绵的嗓音唱流行歌曲颇令人陶醉。
另外,她长得非常漂亮。从她结婚时的一幅精美照片看,她的容貌漂亮得无可挑剔,发辫又粗又光滑,两道弯眉十分动人,一双灰眼睛像埃及人似的,沉静深邃。
这桩婚事就是人们常说的那种“门当户对”。斯科洛多斯基家也因波兰遭不幸而衰败,属于产业极少的小贵族。他家的祖业在华沙以北大约一百公里的斯科洛迪,这是几个庄园的总称。几个世家都姓斯科洛多斯基。按照昔日非常流行的风俗,庄园主应该授权佃农使用其族徽。
这些家族的自然职业便是耕种土地,遇上混乱时期,田产收获减少,原先的富裕渐渐不存在了。在十八世纪,伏拉迪斯拉夫·斯科洛多斯基的直系祖先拥有好几百英亩土地,生活安乐无虞,几代子孙也享受着富裕的农场主生活,可这位年轻教师的父亲约瑟夫却没享过清福。这位斯科洛多斯基先生渴望改善自家生活,也让自己引为自豪的姓氏重新显赫,于是他弃农从教;战争和革命的波动过后,他在卢布林这座重镇的一所男生中学当了校长。他是这家的第一个文人。
博古斯基和斯科洛多斯基两家子女都多,博古斯基家有六个子女,斯科洛多斯基家有七个。儿女中有当农民的、有当中学教师的、出了一个律师,还有一个出家当修女的……其中也出了几个不务正业的。一个是斯科洛多斯卡夫人的弟弟亨利克·博古斯基,这人对艺术着了迷,自以为天赋过人,决意从事这种最靠不住的行当。斯科洛多斯基老师也有一个类似性情的弟弟。这个乐天派年轻人名叫斯德齐斯拉夫·斯科洛多斯基,是个对一切事情都满不在乎的家伙,先后在彼得堡当过律师,在波兰起义中当过兵,起义失败后亡命法国,在普罗旺斯写诗抒怀,在图卢兹得到了法律博士学位,反正他的命运总是飘忽不定。
父母两家的亲属中,鲁莽的稳重的都有,有的人沉稳有见解,有的人头脑发热爱闯荡。
玛丽·居里的父母都属于明智的那一半人。父亲效仿祖父从教,在彼得堡大学钻研理科,回华沙后在学校教数学和物理。母亲办学相当成功,城里上等人家纷纷把女儿送来上学。她那所女子学校在弗利塔街,全家在教学楼的第二层住了八年。父母住的卧室窗外有长长的阳台,上面的一圈花草十分鲜艳。每天早上,这位当校长的母亲走出卧室,前面几间教室已经回荡着叽叽喳喳的交谈,女学生们在等着上第一节课了。
一八六八年,伏拉迪斯拉夫·斯科洛多斯基离开这所学校,成为诺佛立普基路上那所高中的教师和副督学,他的妻子也不得不适应新的生活了。丈夫有了新工作,得到了分配给他们的新住房,住在这里,她就不可能既照顾自己的五个孩子,又担起校长的职责。斯科洛多斯卡夫人不无遗憾地辞去女子中学的职务,迁出弗利塔街的那所房子。就在搬出这里前几个月,一八六七年十一月七日,她生下了玛丽·居里——也就是昵称玛妮娅的小姑娘。
“哟,安秀佩西奥,睡着啦?”
玛妮娅蜷缩在母亲面前的脚凳上,摇了摇头说:
“没有,妈妈。我醒着呢。”
斯科洛多斯卡夫人伸出轻柔的手指,又摸了摸小女儿的额头。玛妮娅心里清楚,这是妈妈最亲昵的表示了。从玛妮娅开始记事起,妈妈就没有吻过她。她最大的幸福就是蜷缩在尽量靠近母亲的地方,不知所措地体会着母亲迷人的沉思,想从难以察觉的细微表示中感觉妈妈对自己博大的慈爱,以及妈妈对幼小女儿命运的关注。她仅仅希望得到母亲说出一两个字眼,脸上露出一丝微笑,朝自己投来亲昵的一瞥。
她并不懂得母亲为什么疏远自己的孩子们,不明白母亲这么做的可怕根源,然而,斯科洛多斯卡夫人这时已经病入膏肓。玛妮娅出生时,母亲已经露出肺结核的苗头,如今五年过去了,虽然她既请教医生又治疗调养,但病情还是在加重。斯科洛多斯卡夫人是位有勇气的基督徒,决心尽量不让家人留意到她遭受的病痛。她衣着整洁,总是有精有神,一如既往过着家庭主妇忙碌的生活,给大家一个身体健康的印象,不过,她对自己立下严格的规矩,自己使用单独的餐具吃饭,决不拥抱亲吻儿女。斯科洛多斯基家的孩子们对她的可怕疾病所知甚少,只能听见她不时从自己的屋子里传出几声猛烈的干咳,只能偶尔从父亲脸上看到一片忧郁的愁云,发现如今的睡前祷告辞中增加了短短的一句话:“愿主保佑母亲健康。”
年轻的母亲站起身,把孩子抓在自己身上的稚嫩小手推开。
“放开我,玛妮西娅……我忙着呢。”
“我待在这儿好吗?我……我想看书。”
“我看你最好去花园玩,今天天气多好啊!”
玛妮娅一说到看书,脸蛋上就浮出格外羞怯的红晕。一年前全家住在乡下的时候,布罗妮娅觉得独自学习字母无比乏味,灵机一动想拿妹妹作个试验,跟妹妹玩上课游戏,自己当教师。两个小女孩用纸板剪的字母随意拼单词,饶有兴致地玩了好几个礼拜。一天早上,布罗妮娅当着父母的面念一段非常简单的文字,读得结结巴巴。玛妮娅听得不耐烦,从她手中夺过那本书,大声念出那页的第一句。大家一时惊得说不出话来,她心里得意,继续玩这个有趣的念书游戏。突然,她慌了,朝周围扫了一眼,只见父母露出诧异神色,布罗妮娅脸色阴沉,正瞪着她。她含混不清嘟囔着,忍不住抽泣起来,虽然她颇有神童的天才,却只是个四岁的小娃娃。她哭得伤心极了,边哭边喃喃道:
“原谅我……原谅我吧!我不是故意的。不是我的错……不是布罗妮娅的错!只是这段话太简单!”
玛妮娅忽然感到一阵失望,因为学会了念书,大家没准儿再也不会原谅她了。
这次难忘的小事过后,这个小女孩渐渐认准了字母,只是由于父母总是巧妙地避免让她接触书籍,所以她并没有认识多少字。父母是谨慎的教师,害怕自己的小女儿智力发育过早没好处。遇上她伸手指向家里丰富的大字印刷书本,父母就劝她:“去玩玩积木吧……你的布娃娃呢?玛妮娅,给我们唱支歌吧。”今天母亲又对她说:“我看你最好去花园玩。”
玛妮娅朝刚才穿过的那扇门瞅了一眼。里面传来积木落在地板上的哗啦啦响声,还有门子隔不断的喧嚣声。看来没人会陪她散步了。去厨房也没希望找到陪她玩的人,因为她听见厨房里人们闲聊,炉盖叮当乱响,知道佣人们正在准备晚饭。
“我去找苏西娅。”
“随你吧。”
“苏西娅……苏西娅!”
姐妹俩手拉手穿过狭窄的小院子,她们每天都要在这里玩捉迷藏和蒙眼抓人的游戏。经过学校的几座房子后,她们来到一个平整的大花园外,花园有个虫蛀的木大门。
一阵淡淡的乡村泥土气息,透过墙里面的树木和稀疏小草散发出来。
“苏西娅,我们要去兹窝拉了吧,是不是很快就走?”
“不到时候呢,七月前不会去。你还记得兹窝拉?”
玛妮娅有着惊人的记忆力,能回忆起在那里的一切:去年夏天她和姐姐们在那里的小河里划船,一玩就是几个钟头……她们悄悄捏泥巴,把衣服上围裙上溅满了黑糊糊的泥点,然后把捏好的泥塑放在只有她们知道的一块木板上晒……有时候七八个小调皮鬼同时爬上那棵老菩提树,有她们的表兄妹和小朋友们,她还太小,胳膊腿儿不够长,小朋友们就把她举上去……大树枝上垫着凉凉的卷曲白菜叶,枝叶间平铺白菜叶,上面晾开他们带来的醋栗、鲜嫩的生胡萝卜、樱桃等……
她还记得在马基的事情,当时约瑟夫去一个燥热的谷仓里学习乘法表,孩子们还想把玛妮娅埋进流动的谷粒堆……那里有斯科兹波夫斯基老爹,他赶大马车的时候,鞭子甩得噼啪响!还有克萨维尔叔叔的马儿……
孩子们每年都能在乡下度过一段让他们着迷的假期。事实上,在这个庞大的家族中,只有一小支住在城里,斯科洛多斯基一家在乡下的亲戚无计其数。每个省里都有姓斯科洛多斯基和姓博古斯基的亲戚在耕种一小片波兰的土地,他们的房屋并不华丽,不过都有富余屋子,可以让教师一家在天气好的日子里住。虽然玛妮娅的家境并不宽裕,可她还是积累了不少度假知识。华沙市民每逢假期就频繁光顾这种廉价的“度假胜地”。到了夏天,两位教师的这个小女儿就变成个能吃苦耐劳的小农民——这倒很符合她的家族根深蒂固的本能。
“我们赛跑吧。我打赌,我准能比你先跑到花园那一头!”苏西娅神色一本正经,俨然在扮演“母亲”角色。
“我不想跑。你给我讲个故事吧。”
论讲故事,谁也比不上苏西娅,就连当教师的父亲和母亲也比不上。她的想象力丰富,能把每一桩轶事、每一个童话故事讲得活灵活现,就像高手演奏的华彩变奏曲。她还自编喜剧小品,兴致勃勃地当着姐妹和弟弟的面表演。苏西娅的创作与表演天赋几乎征服了玛妮娅。玛妮娅入神地听着姐姐讲的神奇冒险故事,时而咯咯发笑,时而浑身颤抖。故事的线索复杂,五岁儿童要想完全听懂并非易事。
两个女孩走上回家的路。她们走到离高中区不远的地方,姐姐本能地放慢脚步,压低声音。苏西娅高声讲出的自编故事并没有讲完,可她不吱声了。两个孩子悄没声地从学校右面一律挂着硬花边窗帘的窗户前面走过。
这是校长伊万诺夫先生家的窗户,他是沙皇政府在这所学校的代表。
波兰人在一八七二年沦为“俄国臣民”,命运十分悲惨。感觉敏锐、情绪冲动的知识界更加不幸,对于强加给波兰人的屈辱,这些人比社会其他阶层更感到痛苦,也从来没有停止过酝酿反抗。
整整一个世纪之前,波兰的国力大大衰落,几个贪婪而强大的邻国君主决定了波兰毁灭的命运,一连三次入侵后,德国、俄国和奥地利将波兰肢解吞并掉了。波兰人组织过几次反对压迫者的起义,结果却是将囚禁自己人民的锁链捆得更紧。一八三一年英勇的革命过后,沙皇尼古拉饬令,在波兰的俄国占领区采取严厉报复手段。大批爱国者被监禁、被流放,财产被没收……
一八六三年又举行了一场起义,结果导致了又一次灾难。起义者手中只有铁锹、镰刀、木棍,他们的对手沙皇军队却有马枪。拼死斗争持续了十八个月,最后,五位起义领袖被吊死在华沙城墙的绞架上。
那以后,俄国采取种种手段,压迫不愿屈服的波兰人民。大批上了枷锁的起义者被押送到西伯利亚流放地,同时,大批警察、教师、官吏像潮水般涌进波兰各地。他们的使命是监视波兰人民,迫使人民接受他们的宗教,查禁可疑书籍和报纸,渐渐废除使用波兰的民族语言……总之,他们要摧毁人民的意志。
但是,在另一个阵营里,抵抗活动的组织十分迅速。由于那几次灾难经历,波兰人明白无法通过武装斗争重获自由,至少眼下还不行。因此,他们的任务就是等待时机,并且在等待时期消除人们的怯懦和灰心情绪,这两种情绪是十分危险的。
因此,战斗的形式改变了。以前的英雄是手持镰刀冲向哥萨克人的勇士,他们牺牲前就像著名英雄路易斯·纳尔布特一样,高喊:“为祖国牺牲多么幸福!”而现在的英雄则是艺术家、牧师、学校教师等有识之士,新一代的思想要靠他们来引导。这些人的勇气在于忍辱负重,在于迫使自己以伪装的身份留在沙皇能够容忍的位置上,秘密影响青年一代,引导爱国者。
因而,在整个波兰的所有学校中,一方是斯科洛多斯基这样的被征服受压迫的教师,另一方是伊万诺夫这种当密探的征服者校长,两方面看上去情深谊笃,骨子里却相互敌对。
在诺佛立普基路上的这所学校中,统治者伊万诺夫尤其可恶。他对自己的属下毫不留情,教师们被迫教本国学生学习俄国语言,伊万诺夫对教师们软硬兼施,有时用甜言蜜语恭维,有时则野蛮训斥。这是个无知的家伙,一时兴起也会检查走读学生的作文,追查小男生一时疏忽流露出的“波兰词语”。有一天老师为自己的学生辩护,平静地对校长说:
“伊万诺夫先生,孩子出错纯属疏忽……其实你写俄文也会出错,而且常常会出错。我相信你也像这些孩子们一样,不是故意要出错。”这以后,校长与斯科洛多斯基老师的关系就变得非常冷淡。
苏西娅与玛妮娅散步回家后悄悄溜进父亲的书房,父母正在谈论这位伊万诺夫。
“你还记得二年级男生上星期在教堂做弥撒的情形吗?当时的话题是‘神保佑他们实现自己最热切的愿望’。他们自行募捐支付这次弥撒的费用,还不愿把自己特别的愿望告诉牧师。昨天,小巴金斯基把实话都对我说了,他们听说伊万诺夫的女儿得了伤寒,因为他们恨这个校长,就专门做弥撒咒他的女儿送命!要是那个倒霉的牧师知道了真情,准会为自己卷入孩子们的阴谋大呼上当!”
斯科洛多斯基先生为这事感到喜悦,可他的妻子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并不感到可笑。她低头做手头的粗笨活计。斯科洛多斯卡夫人拿着割皮刀和锥子,正在做鞋子。她从来没觉得有什么活计自己不该做,这是她的一种特殊性格。几次怀孕加上生病,她只好待在屋子里,便学会了鞋匠手艺。孩子们的鞋子很快就磨坏了,学会这手艺后,除了买皮子就用不着花买鞋的钱了。毕竟生活是艰难的……
“玛妮西娅,这双鞋是给你的。你看,穿上这双鞋,你的一双小脚一定非常好看!”
玛妮娅望着母亲那双纤长的手切下鞋底,吃力地用线来回缝。她父亲刚刚在旁边那张扶手椅上舒舒服服坐下,这是他最喜爱的座位。要是能爬上父亲的膝盖,把他仔细打好的领带弄乱,要不就拽拽他和蔼大脸周围的棕色胡须,那一定很有趣。
可是大人们正在谈论非常烦人的话题:“伊万诺夫……警察……沙皇……流放……密谋……西伯利亚……”自从玛妮娅来到这个世界上,就天天听到人们说这些字眼,她隐隐约约感到这是些可怕的事情,本能地躲避开,不愿提前弄明白。
这个小女孩沉浸在自己幼稚的幻想中,转身离开父母,不听他们穿插在割皮声和钉鞋声中的低声亲昵交谈,扬起脑袋在屋子里到处走动,活像马路上无所事事闲逛的人,在自己特别喜欢的东西前停住脚步。
这是全家最好的一间屋子,至少玛妮娅觉得这里最有趣。那张红木写字台是法国样式的,那把覆盖着结实红丝绒的扶手椅是复辟时期的式样,这些让她心里充满了敬意。这些家具多么清洁光亮啊!将来玛妮娅长大上学了,就能在这张教师备课用的大办公桌上占有一个位子,这是斯科洛多斯基老师的办公桌,每天下午孩子们都聚在周围做作业。
屋子一侧的墙壁上挂着一幅神色庄严的主教画像,金色的画框非常笨重,他们家认为这画出自提香(1)之手,当然只有他们家有此看法。玛妮娅对这画不感兴趣,她欣赏的是桌子上那只胖嘟嘟亮闪闪的翠绿色孔雀石座钟,还喜欢一位表哥前一年从意大利巴勒莫带来的圆桌。桌面的图案像个棋盘,每个小方格都是用纹理不同的大理石镶嵌的。
小姑娘从一个架子旁绕过去,这个架子上陈设着一个饰有路易十八慈眉善目画像的法国塞夫勒瓷杯。大家一再告诉玛妮娅不要碰这架子,她见了这东西就觉得害怕。最后她在自己最喜爱的宝贝跟前停下脚步。
其中一个是挂在橡木壁板上的精密气压计,白色度盘上,镀金长指针闪闪发亮。在某些日子里,教师就在聚精会神的孩子们面前仔细调整它,把它擦拭干净。
另一个是装满了精美奇怪仪器的玻璃门柜子,里面有玻璃试管、小天平、矿物标本、还有个带金箔的验电器……斯科洛多斯基老师以前常带着这些东西进教室,但是,由于政府减少了科学课程的课时数,这个玻璃门柜子就总是紧紧关闭着。
玛妮娅想不出这些神奇的小东西有什么用。一天,她踮着脚尖,望着里面的东西,不禁着了迷。爸爸扼要地告诉她这些东西的总称:“物理……实验……仪器”。
多滑稽的名字啊!
她没有忘记这个字眼,因为她从来不会忘记任何事情。她当时兴致正浓,就把这几个字眼当作歌谣哼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