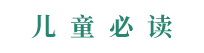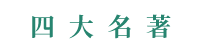第二章 黑暗的日子
“玛丽亚·斯科洛多斯卡。”
“到。”
“概述一下斯塔尼斯拉斯·奥古斯特的事迹。”
“斯塔尼斯拉斯·奥古斯特·波尼亚托夫斯基于一七六四年被推选为波兰国王。他非常英明,受过良好的教育,与艺术家和作家交朋友。他了解造成波兰王国衰落的种种弊端,努力纠正国家的混乱状态。不幸的是,他是个缺乏勇气的人……”
站起来回答问题的女学生看上去与其他同学没什么两样,不过,她背诵课文时语调清晰,口吻坚定。她的座位在第三排,靠近一扇大窗户,窗外是萨克森尼花园白雪覆盖的草坪。这个十岁小女孩身穿寄宿学校的海军蓝哔叽制服,系着铁纽扣,戴着浆硬的白领子,举止显得拘谨。昵称叫做安秀佩西奥的小姑娘原来是一头乱蓬蓬的卷发,现在梳成紧紧的发辫,末端扎着一条窄丝带,两边散乱的卷发拢到娇小可爱的耳朵后面,一张任性的小脸蛋看上去显得没什么特别。她姐姐海拉坐在旁边的座位上,海拉也梳了一条发辫,只是比妹妹的辫子粗一点,卷发的颜色也深一些。整齐划一的制服、严格简朴的发型,这是西科尔斯卡小姐“私立学校”的规矩。
坐在前面椅子上的教师安妥尼亚娜·杜巴尔斯卡小姐身穿的服饰也不轻佻。她身穿黑稠上衣、鲸须衣领,绝对不属于流行款式。这位小姐根本谈不上美丽,她脸色阴沉,神情粗野,长相丑陋,不过倒能激起别人的同情。平常人们以“杜普西娅”称呼杜巴尔斯卡小姐,她是算术和历史教员,兼任学监,因此有时不得不采用强制手段,对付小斯科洛多斯卡的独立精神和固执性格。
不过,她低头望着玛妮娅的时候,眼神中还是充满了慈爱。她怎么能不为如此出色的学生感到自豪呢!这个学生比所有同班同学都小两岁,可她学习任何课程都似乎不觉得困难,算术第一、历史第一、文学第一、德语第一、法语第一、课堂回答第一……
教室里鸦雀无声——甚至还不只是鸦雀无声而已。历史课上有了一种激越的热烈气氛。二十五个一动不动的年轻爱国者露出激昂的眼神,杜普西娅老师绷起脸显出庄严神色,大家都反映出真诚的热情。提到多年前逝世的一位国王,玛妮娅的背诵口吻变成了诵诗般的声调,带着特别的激情:
“不幸的是,他是个缺乏勇气的人……”
相貌平平的女教师在用波兰语教波兰史,她和过分严肃的学生都露出一种神秘的表情,仿佛大家都是一桩密谋计划中的同盟。
突然,大家都像密谋败露时的同盟者一样惊得目瞪口呆:楼梯那边传来一阵电铃声。
两声长,两声短。
断续的信号立刻引起一阵骚动。杜普西娅警觉起来,匆匆收拾起铺开在椅子上的书籍,大家行动敏捷,七手八脚把波兰文的书籍和笔记本从课桌上收拾起来,放进四个动作敏捷的女生围裙里,四个女孩托着围裙穿过一扇通往寄宿宿舍的小门。接着是一阵挪动椅子的声音和课桌打开又关上的声音……四个女生气喘吁吁跑回来,坐在自己的位置上。这时,通往前厅的门慢慢推开了。
霍恩伯格先生出现在门口。他身穿做工讲究的镶边制服——黄色长裤、蓝色上衣、衣服上的纽扣闪闪发亮。霍恩伯格是华沙城各私立寄宿学校的巡察官。他身材粗壮,留着德国式样的头发,一张肥胖的脸上两只锐利的眼睛从金边眼镜后面扫视着。
这个巡察官望着学生,一句话也不说。陪在他身旁的是校长西科尔斯卡小姐,她也望着大家,表面上十分镇静,不过显得稍有些焦虑。今天的信号发得太晚了,工友刚刚发出信号,霍恩伯格就抢在带路人前面登上楼梯,闯进教室。不知道是不是一切都安排好了。
一切都安排好了。二十五个小姑娘正低头做女红,指头上戴着顶针,在一块块毛边方布上仔细练习锁扣眼,线缝得无可挑剔。空荡荡的书桌里除了剪刀和散乱的线轴外,什么别的东西也没有。杜普西娅脸色发青,额头上青筋暴露,双手支在前面的讲台上,面前放着一本打开的书,是用合法文字印的。
女校长口吻平静地说:“巡察官先生,孩子们每星期上两小时缝纫课。”
霍恩伯格朝教师走去。
“你刚才在大声朗读,小姐。读的是什么?”
“克雷洛夫的《寓言》。我们是今天才开始学的。”
杜普西娅的回答十分镇静,脸色也渐渐恢复了常态。
霍恩伯格一副漫不经心的模样,伸手打开旁边一张书桌的盖板。里面什么也没有。没有纸张,没有书本。
女孩子们缝完最后一针,把针别在布上,结束了缝纫活儿。大家双臂交叉,坐在座位上一动不动。学生们身穿同样的深色服装,戴着白衣领,二十五个女孩的面孔仿佛突然变得成熟了,坚定的神色下面掩盖着恐惧、狡黠和憎恨。
霍恩伯格先生一屁股跌坐在杜巴尔斯卡小姐让给他的椅子上。
“请你叫一个女孩过来。”
坐在第三排的玛丽亚·斯科洛多斯卡本能地把惊慌的小脸扭过去望着窗外。心里在默默祈祷:“上帝,求求你,让别人去吧……别叫我……别叫我。”
可她知道得很清楚,叫的人准是她。每次政府巡察官员来,都会叫她回答问题,因为她了解的东西最多,而且俄语讲得最标准。
听见叫她的名字,她站起身。她觉得燥热,又觉得浑身冰凉,一阵强烈的屈辱感让她的喉咙哽噎了。
“背诵祈祷文。”霍恩伯格先生生硬地说,他的态度显出冷漠和厌倦。
玛妮娅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地背诵了“我们的在天之父”,不过内容完全正确。沙皇发明的最微妙的一种侮辱方法,就是迫使波兰儿童每天用俄语念天主教祈祷文。因而,在假装尊重波兰人信仰的借口下,他其实在亵渎他们的自豪感。
一片寂静。
“说出叶卡捷琳娜二世以后统治我们神圣俄罗斯的皇帝名字。”
“叶卡捷琳娜二世、保罗一世、亚历山大一世、尼古拉一世、亚历山大二世。”
这位巡察官感到满意。这孩子记性不赖。发音真棒,简直像是在圣彼得堡出生的。
“说说皇族的名字和称号。”
“女皇陛下、亚历山大太子殿下、大公殿下……”
听她按序说完一长串名字,霍恩伯格脸上露出淡淡的微笑。心想,真是太好了。这家伙既看不出也不愿留意玛妮娅心中的痛苦,她板起面孔,竭力掩盖起心中的反抗情绪。
“沙皇在爵位品级中的尊称是什么?”
“陛下。”
“那么我的尊称该是什么?”
“阁下。”
巡察官喜欢提这些等级上的小问题,觉得比算术或拼写更重要。出于自己消遣取乐的原因,他再次问道:
“我们的统治者是谁?”
校长和学监都垂下眼皮盯着手里的花名册,为的是掩饰眼中的怒火。回答有些迟疑,霍恩伯格恼火了,再次大声问道:
“是谁在统治我们?”
“亚历山大二世陛下,全俄罗斯的沙皇。”玛妮娅的声音露出痛苦,脸色变得煞白。
提问结束了,这位官员点了点头,起身离开座位,朝隔壁教室走去。西科尔斯卡小姐陪在后面。
杜普西娅抬起头。
“过来,我的小人儿……”
玛妮娅离开自己的座位,走到老师跟前,女教师一句话也没说,俯身动情地亲吻着她的额头。教室里的生命重新复活了,这个神经几乎绷断的波兰小女孩突然放声大哭起来。
“巡察官今天来过!巡察官今天来过!”
情绪激动的孩子们放学时纷纷把这则消息告诉等着接她们回家的母亲和保姆。在今冬第一场雪覆盖的人行道上,一群群包着头巾的小姑娘和身穿毛皮大衣的成人很快散去。她们说话时全都压低声音,每一个闲散的路人、每一个玻璃橱窗前闲逛的人都可能是警察的密探。
来接两姐妹的是米哈洛夫斯卡夫人,就是卢西娅姑妈。海拉兴致勃勃对她说起上午发生的事情。
“霍恩伯格向玛妮娅提问,她的回答棒极了,可她后来哭了。这个巡察官好像没有批评任何一个班。”
海拉情绪激动,喋喋不休低声说个没完,可玛妮娅只是静静地跟在姑妈身边走着。巡察官盘问她之后已经过了好几个钟头,可这个小女孩仍然觉得难受。她憎恨这些突如其来让她感到的惊恐,搞这种表演不得不说谎,她感到屈辱,说的都是谎言……霍恩伯格的视察让她今天更加深切地感到了悲哀。难道她还能回忆起自己曾是个无忧无虑的顽童?一系列的不幸接连朝斯科洛多斯基一家袭来,玛妮娅觉得,过去四年简直如同一场噩梦。
先是妈妈带着苏西娅去了法国尼斯。大家对玛妮娅解释说:“妈妈医治后,病就全好了。”一年后母女再次见面,她几乎不相信这个被命运无情捉弄的衰老妇人就是自己的母亲……
接着,一八七三年秋季,他们度假回来那天是个难忘的日子。斯科洛多斯基先生带着全家返回来,见书桌上摆着一封公函:奉当局命令,降低他的薪水,革去他副督学的职务,依职务分配的住房也一并取消。他被降职了。这是伊万诺夫校长在报复他,报复这位不愿奴颜婢膝服从命令的下属。这场战斗他打胜了。
后来,斯科洛多斯基一家搬迁过几次,最后定居在诺佛立普基路和加迈利特路交叉口一所拐角套房里。原来恬静亲密的生活环境渐渐为贫困打破了。斯科洛多斯基老师开始收寄宿学生,起初是两三个学生,后来增加到五个、八个、十个,都是他自己的学生。他在家里供给他们食宿,对他们个别辅导。这个家变得像个吵闹的磨坊,家庭生活的亲密气氛消失了。
家里不得不做出这种安排,一来是因为斯科洛多斯基先生降了职,二来还因为他必须做出牺牲才能支付妻子在法国里维埃拉疗养的费用。迫于急需金钱,这位向来谨慎的教师听从了一个倒霉蛋内弟,冒险投资一种所谓“神奇”蒸汽磨坊,结果全部积蓄三万卢布很快便丧失殆尽。此后,他为过去的愚蠢懊悔,为将来的前景担忧,时时心中内疚,不断责备自己,悔不该把家境搞得如此贫穷,不该弄得女儿们没有了嫁妆。
不过,玛妮娅突然真正认识到家庭的不幸,还是在两年以前。当时一个寄宿生把斑疹伤寒传染给布罗妮娅和苏西娅。接下来的几个星期真可怕!在一个屋子里,母亲尽量控制住自己的阵阵狂咳;在另一个屋子里,两个小女孩发着高烧,浑身颤抖,不停地呻吟。
在一个星期三,当教师的父亲把约瑟夫、海拉和玛妮娅带去最后一次看他们的大姐姐。苏西娅身穿白色衣服,躺在灵柩中,脸上毫无血色,仿佛还露出一丝微笑,头发剪得很短,但容貌仍然非常美丽。
这是玛妮娅第一次见到死人,也是平生第一次身穿黑色小外衣给人送葬。布罗妮娅尚未痊愈,趴在枕头上哭,斯科洛多斯卡夫人也因为身体虚弱得不能出门,只能隔着窗户目送自家孩子的棺木沿加迈利特路缓缓运走。
“孩子们,我们要多走一段路。我要趁大冷天到来之前买些苹果。”
这位好姑妈卢西娅带着她的侄女们,步履轻快地穿过萨克森尼花园。在这个十一月的傍晚,花园里几乎一个人也没有。她总是找各种借口,想让孩子们多呼吸点新鲜空气,尽量让孩子们远离患肺结核的母亲居住的狭小房子。万一她们也传染上可如何是好!海拉看上去很健康,可玛妮娅却面色苍白,神情忧郁。
三个人走出花园后,来到华沙的旧街区,玛妮娅就出生在这个地方。这儿的街道比新城区有意思多了。在旧米亚斯托广场附近,一个个白雪覆盖的倾斜大屋顶下,灰色楼宇正面装点着无数雕饰:精致的檐口、圣徒的面部雕像、表示客栈或商店的动物形象等。
冰冷的空气中,教堂钟声此起彼伏,声调各异。这些教堂让人回忆起玛丽亚·斯科洛多斯卡整个逝去的童年时光。她在圣玛丽教堂受洗礼。她第一次领圣餐是在多米尼加教堂,那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玛妮娅和表姐亨利埃塔都发誓不让牙齿接触到圣餐饼干……小姑娘们还常常在星期日去圣保罗教堂,听神父用德语讲道。
寒风刮过的新米亚斯托广场空空荡荡,玛妮娅对这里也很熟悉。她家搬出那个体育场后,曾在这附近住过一年。当时,她天天跟母亲和姐姐们去圣母小教堂。那是个奇特而迷人的教堂,台阶都是用红色石块砌成的,几个世纪的践踏磨蚀了台阶,方尖塔和教堂主体建筑越往上越宽大,最高处可俯瞰下面的河流。
卢西娅姑妈做了个手势,两个小姑娘今天又一次走进这座教堂。穿过狭窄的哥特式大门后往前走了几步,玛妮娅便颤抖着跪倒在地上。不能随苏西娅一起到这里来,让她心中十分痛苦。如今,苏西娅已经与世长辞,上帝毫不怜悯的母亲也受到莫名其妙的磨难不能前来。
玛妮娅相信,自己的祈祷再一次传进了上帝的耳朵。她热烈恳求耶稣把生命赐给她在世界上最爱的人。她向上帝表示,只要能拯救斯科洛多斯卡夫人,她愿意献出自己的生命,替妈妈去死。卢西娅姑妈和海拉靠在她旁边,也在俯首低声祈祷。
三个人分别走出教堂,一起沿高低不平的台阶拾级而下,朝河边走去。宽广的维斯杜拉河展现在她们面前,黄水滚滚,浊浪翻腾,流过河中沙洲,拍击不规则河岸边洗衣服用的澡盆和木筏。夏日里一群群快乐的青年泛舟的划艇此时全系在河边,船具都卸掉了。河边只有运苹果的货船停靠处是热闹的地方。走到跟前,见这里有两条运苹果的货船,船货很沉,船沿几乎贴近水面了。
船长身穿厚厚的羊皮袄,推开一捆捆防冻的柔软干草,让人们看他的货色。只见下面的红苹果个个闪闪发亮。船舱里装满成千上万的苹果。苹果是从维斯杜拉河上游美丽的喀兹米尔兹城运来的,经过许多个日日夜夜的长途航行才运到这里。
“我要去挑苹果!”海拉嚷道,玛妮娅立刻学着她的样子,把手从暖手筒里抽出来,放下肩膀上背的书包。
这次活动比任何事情都更让两个小姑娘高兴,其中的每一个细节都让她们着迷。她们把一个个苹果拿在手里,翻来覆去仔细察看,通过检验的便丢进一个大柳条筐里,发现了烂苹果就使出全身力气扔进维斯杜拉河,望着红红的果子沉下去。等到柳条筐装满了,才抓起一只最好的苹果下船。苹果又冷又脆,咬一口味道美极了。卢西娅姑妈讨价还价付了款,然后从一群脸上长着雀斑的顽童中找一个帮忙,把这筐珍贵的食品送回家。
时间是五点钟。吃完茶点后,佣人收拾干净桌子,点上煤油吊灯。工作的时间到了。寄宿学生三三两两聚在他们居住的屋子里。教师的儿女们就待在兼做书房的餐厅里,打开书本和练习册。几分钟后,房子里到处都响起了烦人的嗡嗡读书声。在许多年里,这一直是这所房子里的生活主旋律。
往往有几个学生禁不住要结结巴巴念出拉丁语的诗句、历史事件的日期、问题的答案等等。在这座知识工厂的每一个角落里,都有人在呻吟,在痛苦挣扎。功课实在太难了!斯科洛多斯基老师不得不常常安慰产生绝望情绪的学生,这些学生用本国语言完全能理解一种论证,可使用官方语言俄语写的东西却费尽心机也弄不懂,要想用俄语复述出来就更无可奈何了。
小玛妮娅却没有体会过这种苦恼。她的记忆力超常,同学们见她一首诗歌只要念上两遍,就能一字不落地背诵出来,以为她是骗她们,指责她背地里悄悄学诗歌。可她完成其他作业也比她们快得多,往往因为完成作业后无所事事,或者出于善良天性,帮助功课吃力的同伴解决困难。
她最喜欢做的事还是读书,今天晚上她就是这样,拿着一本书坐在大桌子旁边,胳膊肘支在桌子上,两手捂着额头,两个拇指堵住耳朵,免得听到海拉的嚷叫。海拉要是不大声朗读,就不能温习功课。不过,玛妮娅的预防措施纯属多余,因为她读书只要读进去,就再也感觉不到周围发生的事情了。
全神贯注是这个健康女孩的唯一特长,这也让她的姐姐和朋友找到了拿她取乐的把柄。有十几次,布罗妮娅与海拉合谋在妹妹周围发出让人难以忍受的喧闹,却从来不能让她抬起头看一眼。
今天,她们想要使用一种特别手腕,认为肯定管用。卢西娅姑妈的女儿来访,这也引起她们特别想搞恶作剧的冲动。两个姑娘踮着脚尖走过去,在全神贯注读书的玛妮娅周围用椅子堆成个架子。先是每边放两把椅子,然后再往上垒一把,然后在这三把椅子上再堆两把,最后在上面横放一把椅子盖个顶。完事后两姐妹退避开假装在做作业,等着看笑话。
她们不得不等待很久,因为妹妹什么都没有发现,既没有注意到她们的窃窃私语,也没有留意她们压抑的嗤笑声,甚至对脑袋上方的椅子投下的阴影都没感觉到。这种状况一直保持了半个钟头,玛妮娅受到威胁,一个不稳定的金字塔就要在她脑袋上方坍塌,可她丝毫也不知道。等到读完了一章,她合上书抬起头——椅子堆如海啸地震般坍塌了,落在地板上蹦跳着。海拉乐得又笑又叫,布罗妮娅和亨利埃塔灵活地跳起身做防御准备,怕她反扑过来。
可是玛妮娅一动也没动。她根本不会发火,可是,这种吓人的恶作剧也没让她觉得有什么好笑。她一双灰色眼睛露出的神色仿佛突然惊醒的梦游者。一把椅子砸在她左肩上,她揉了揉肩膀,捡起书走向隔壁,从几个“大姑娘”跟前走过时,只是简单说了句:
“真荒唐!”
“大姑娘”们对这句结论并不满意。
也许只有在这种完全忘我的境界下,玛妮娅才能找到她童年时期感到无比惊奇的事物。她如饥似渴地见什么读什么,诗歌、学术著作、冒险故事、从父亲的图书馆里借来的技术著作等等。
虽然时间不长,但她可以不时将心中阴沉沉的愁绪排遣一下,暂时忘记俄国密探,忘记霍恩伯格的巡察,忘记沉重负担给父亲留下的愁容,忘记家里的嘈杂,也忘记了每天黎明就得揉着惺忪睡眼摸黑从漆布沙发上起床,好让寄宿生在她和哥哥姐姐们睡觉的餐厅里吃早饭。
她忘记了恐惧,忘记了对压迫者的恐惧,忘记了宗教上的恐惧,忘记了对疾病和死亡的恐惧。她本能地渴望逃避这种令人窒息的“气候”。
然而这种时候十分短暂,她的意识一恢复,一切痛苦立刻回到她心中——首先是母亲的疾病给这个家带来的永恒阴影。母亲以前那么美丽,如今却只剩一个影子了。大人们对玛妮娅说许多安慰的话语,可她已经清楚地感到,自己热烈的敬慕、无限的热爱、虔诚的祈祷都无法防止可怕的结局,而且现在越来越近了。
斯科洛多斯卡夫人也想到自己不久于人世,设法防止自己的去世影响全家的生活。一八七八年五月九日这天,她请求医生别再照顾自己,并把牧师请来。只有牧师应该了解这位基督徒的灵魂,了解她要将四个孩子交给挚爱的丈夫照料,了解她对孩子们未来的焦虑,可她如今不得不撇下他们,而小玛妮娅才刚刚十岁……
当着家人的面,她尽量只显出平静神色,在弥留之际的几个小时里,她的外表极其典雅。她如愿以偿地在清醒安详中死去了。当时她的丈夫和儿女都在那间整洁的屋子里,环绕在她的病榻前。她的一双灰色凤眼已经黯淡,逐个注视着受尽哀愁折磨的五张脸孔,这个临终的女人感到自己造成了他们如此巨大的痛苦,因此仿佛在请求他们原谅。
她打起精神向他们逐一告别。最后越来越有气无力。剩余的精力只允许她作一个手势,说短短一句话了。她伸出剧烈颤抖的手,在空中划了个十字,表示对大家的祝福,对送别她的丈夫和孩子们喃喃地一口气说出:“我爱你们。”
玛妮娅又一次穿起黑丧服,心里怀着悲痛,在加迈利特路上那所房子里悲哀地走来走去。如今,生活发生了变化,她一时不能习惯:布罗妮娅住在母亲生前住过的房子里,只有海拉和她仍然睡在漆布沙发上;父亲匆匆雇来一名管家,每天来对佣人发号施令,决定寄宿生的膳食,粗略照顾一下孩子们的衣着。斯科洛多斯基先生把全部空余时间都花在陪伴自己儿女身上,可他对孩子们的体贴比较笨拙,虽然十分感人,却不过是男人的照料而已。
玛妮娅懂得了生活的残酷。对民族是残酷的,对个人是残酷的……
苏西娅死了。斯科洛多斯卡夫人死了。她失去了母亲的慈爱,失去了大姐姐的保护,在这种环境中,她慢慢长大,却一次都没有抱怨过,她从不抱怨自己的生活。她有一颗骄傲的心,不肯听天由命。她跪在以前母亲带领下走进的天主教堂时,心中隐隐升起了反叛的想法。她不再对上帝怀有原先那种敬爱,上帝是不公正的,他强加给她如此巨大的打击,毁灭了她生活中的快乐、幻想和美好的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