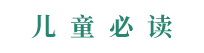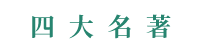第五章 家庭女教师
玛妮娅在一八八五年十二月十日写给她表姐米哈洛夫斯卡的信中说:
亲爱的亨利埃塔:咱俩分手后,我简直像是沦为囚徒了。你知道的,我在勃……律师家找了个工作。这儿简直是个地狱,就是我最仇视的敌人,我也不忍心让他住在这种地狱里。到后来,我与勃……夫人的关系变得非常冷淡,我把这种感觉对她直言相告。由于我们俩相互间的感觉不相上下,所以彼此的了解十分深刻。
这家人跟其他有钱人一样,喜欢撑门面讲法语,背地里却一拖六个月不付账单,其实,他们说的法语就跟法国扫烟囱的人一样低级。在家里,他们连点灯的油都舍不得用,到了外面,却大把乱花钱。他家用了五个仆人。自己装出自由派开明人士的模样,其实他们本质上愚蠢透顶。最可恶的是,他们说话时仿佛嘴上抹了蜜糖,但话里却带着恶意,把人诽谤得体无完肤……我总算在这儿学会了一件事,那就是深刻地认识人。我发现小说里描绘的人物实际上真的有,我也懂得了,人不能跟有财而无德的人交往。
这是一幅毫不留情的画面。由于它出自毫无恶意的玛妮娅之手,我们便看出,她是多么天真,多么富有幻想。她随便选了个富有的波兰人家庭,就希望这家的孩子活泼可爱,家长善解人意。由于她已经准备好要亲近他们,热爱他们,因此她的失望是深重的。
这位年轻家庭女教师写的信,让我们间接感觉到,她不得不离开的自己家那个环境是十分特殊的。玛妮娅在知识分子圈子里遇到过能力平平的人,却从未见过卑鄙的人。她在家里从未听到过一个粗鄙难听的字眼。斯科洛多斯基家的人遇到家庭争吵、人们说恶毒的闲话,总是感到十分惊恐。我们可以想象出,这个姑娘每次遇到愚蠢、琐细或粗鄙的事情,准会感到惊愕和反感。
玛妮娅的哥哥和姐姐都有着高尚的品质和杰出的智力,这一点或许能解开一个困扰我们的谜:为什么没有人发现这个年轻姑娘有着过人的天才和超人的特长?为什么不送她去巴黎就读,却听任她寻找一个家庭教师的职业?
她生活在非凡的人们中间,身边有三个拿到文凭和奖章的哥哥姐姐,他们与她一样,聪明而有志气,热心投身工作。相比之下,未来的玛丽·居里就不显得突出了。在一个有限的知识圈子里,过人的天赋很快就能表现出来,引起人们的惊讶和赞叹,然而,在这个家庭里,约瑟夫、布罗妮娅、海拉和玛妮娅都在成长,在求学问中彼此竞争。因而,当时不论是上了年纪的人还是年轻人,都没有从几个孩子中看出伟大人物的征兆,谁也没有为他们最初的光辉所感动。人们谁也没想过,玛妮娅在本质上会与哥哥姐姐不同,就连她自己也没想过这个。
她拿自己与家人作比较时,便会感到自惭形秽。但是,当她走进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工作时,她便无法掩饰自己的优越性了。就连玛妮娅自己也看得出这种优越,心里便觉得高兴。这位姑娘蔑视出身和财富,她从来看不起这些东西,然而,她对自己的出身和受过的教育却倍感自豪。后来她在批评一些雇主时,流露出一种轻蔑的态度和天真的骄傲。
玛妮娅不但从第一次经验中归纳出关于人类和“有财无德者”等哲理,而且发现,原先向布罗妮娅解释的计划需要做重大修改。
玛妮娅原本希望,在华沙找个工作能挣到数目可观的收入,而且不必忍受路途奔波之苦。留在城里能减轻她感到的苦难,这意味着她可以待在家的附近,可以天天回家,与父亲说说话,还意味着她能够与流动大学的朋友保持联系,也许还能上夜校听几节课呢。
但是,既然愿意做出牺牲,就不能半途而废。这个年轻姑娘选择的命运还不够严酷,她挣钱不多,开销倒不少,常常预支工资购买日常的小零碎,到了月终,积攒下的钱就所剩无几了。可她还得准备好资助布罗妮娅呢,布罗妮娅已经和玛丽亚·拉可夫斯卡去巴黎求学,住在拉丁区清苦度日。而且,斯科洛多斯基先生退休的日子也快到了,届时老人也需要有人帮助。到时候她可怎么办呢?
玛妮娅并没有长时间迟疑不决。两三个礼拜之前,她听说乡下有个报酬优厚的家庭教师职位。她立刻做出决定:她愿意去那个遥远的乡下,也愿意投身到陌生的地方去。虽然她不得不与亲人分别,在人地两生的地方生活好几年,可这有什么关系?报酬很高,而且在那种偏僻的乡下,生活中几乎用不着花销。
“再说,我喜欢乡下清新的空气!”玛妮娅自言自语道,“以前我怎么就没想到这条路呢?”
她把自己的决定写信告诉表姐:
我闲散的时间不多了。虽然我有过迟疑,但已经做出决定,明天就接受乡下那个位置,从一月开始工作。那个地方在普罗克,年薪五百卢布,从一月一日开始算起。他们以前曾对我提起过这个职位,可我当时没接受。这家人对现在的家庭教师不满意,要我去。很可能我也像那个教师一样,不能让他们感到满意。
一八八六年一月一日,玛妮娅冒着严寒启程了,这是她一生中将要经历的许多残酷日子之一。她勇敢地告别了父亲,再次把自己的邮寄地址重复告诉他:
普扎斯尼兹地方,
斯茨组基镇,
佐先生和佐夫人宅子,
玛丽亚·斯科洛多斯卡收
她登上火车车厢。望着父亲矮小的身影,她脸上还挂着微笑。接着,她忽然跌坐在车厢坐椅上,感觉到孤寂向她袭来。她平生头一回独自外出谋生,完全孤立无援了。
这个十八岁的姑娘突然恐慌起来。这列沉重的火车要把她带到远方一个陌生的房子里,与一个陌生的家庭生活在一起,玛妮娅不由感到羞怯,感到恐惧,浑身都颤抖起来。假如这个新雇主与原先那些雇主一样可恶,她可怎么办?倘若她走之后斯科洛多斯基先生生了病,那可怎么办?她还能再次见到父亲吗?她做出的是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愚蠢决定?这个姑娘蜷缩在车厢里,紧紧靠在车窗跟前,望着苍茫暮色中沉寂的原野向后飞驰,用手揩着流淌不止的眼泪。
坐了三小时的火车后,接着是坐在雪橇上奔波四个钟头。雪橇在笔直的道路上滑过,四野一片冬季的庄严肃穆。佐先生和佐夫人是田产管理人,为沙尔托斯基亲王们管理华沙北部一百公里处的部分农田。玛妮娅在这个冰冷的冬夜抵达他们家门口时已经疲惫不堪,周围的情景几乎像在梦中,朦胧中,她看见这家的男主人身材高大,看见他妻子黯淡的面孔,还有几个孩子盯着看她的好奇眼神。
主人请他喝热茶,亲切问候她。然后佐太太带玛妮娅上二楼,走进给她预备好的房间,佐太太离开后,屋子里只剩下她和随身的一丁点行李。
一八八六年二月三日,玛妮娅在写给表姐亨利埃塔的信中说:
我到佐先生和佐夫人家已经一个月了,算是度过了新环境的适应期。迄今为止一切都很好。佐家的人都好极了。我与这家的大女儿布朗卡成了好朋友,于是我在这里相当愉快。我的学生安齐娅快要满十岁了,是个听话的女孩子,不过让父母宠坏了,不懂规矩。当然,谁也不能指望一切都十全十美……
这地方谁也不工作,人们一心想着寻欢作乐。这家人因为不参加乡邻举办的舞会,反倒成了乡下人的话柄。我刚抵达这里一个礼拜,已经有人说我的坏话了,那是因为我不认识这里的人,拒绝参加在卡尔瓦茨家举办的一次舞会,那可是个谣言制造中心。我没去一点儿也不后悔,佐先生和佐太太参加那次舞会直到第二天下午一点钟才回来。我很高兴逃脱了那场折磨,尤其当时我身体还不太舒服。
这里在主显节前夜(1)举办了一场舞会,我有幸见到不少客人,这些人真是漫画家的好题材,我觉得实在有趣。这里的青年人都乏味极了。女孩子有的呆兮兮从不开口,有的却令人讨厌,看上去还有一些显得比较有见识。现在我渐渐看出,我的朋友布朗卡·佐小姐是一颗罕见的珍珠,她有良好的判断能力,而且对生活有透彻的理解。
我每天工作七小时:四小时教安齐娅,三小时辅导布朗卡。工作时间的确不少,不过没关系。我的房间在楼上,宽大、安静,而且相当舒适。佐家的子女很多:三个儿子在华沙上学,一个在上大学,两个在寄宿中学上学。家里还有十八岁的布朗卡和十岁的安齐娅。另外还有三岁的斯塔斯和六个月大的小女儿玛丽施娜。斯塔斯非常有趣。保姆告诉他说,上帝无处不在。他就露出一脸焦虑神色问:“他会抓住我吗?他会咬我吗?”我们都觉得好玩极了。
玛妮娅没写完这封信就搁下笔离开长窗旁边的书桌,身穿毛衣便冒着严寒走到阳台上。窗外景色仍然让她感到可笑。她出发来这个偏僻乡村之前,满心想着会见到乡村景色,到处是草原和森林,可是,来了这里第一次推开窗户一看,外面却是一只高大的工厂烟囱,浓烟滚滚,遮天蔽日。她心里便觉得滑稽。
周围没有一片庄稼地,也没有一片矮树林。广袤的田野上只有一片接一片的甜菜地。到了秋天,一辆接一辆牛车拉着带有泥土的白色甜菜萝卜,缓缓驶向制糖厂。农民为这家工厂耕耘、播种、收获。克拉西尼茨是个小村子,村里的小农舍都聚集在糖厂黯淡的红砖建筑物周围。就连那条河也成了工厂驾驭的奴隶,流进去是清澈的河水,流出来的却是漂着黑糊糊浮渣的污水。
佐先生是位精通新技术的有名农学家,他控制着二百英亩的甜菜种植。他是个有钱人,拥有糖厂的大部分股票。这家人像周围其他人家一样,最关心的事情就是这家工厂。
其实,这工厂根本算不上有什么规模。尽管在当地引人注目,但是与外省几十家其他企业一样,都不过是些小有规模的企业而已。斯茨组基的地产也很小,二百英亩地产与这里广袤的乡村土地相比,简直是九牛一毛。佐先生家生活富足,但算不得首富。虽然与邻近农场的房子相比,他家的房子比较讲究,但再怎么说也称不上豪宅。那是一座周围常见的旧式别墅,房子低矮,倾斜的屋顶下是阴暗的墙壁,藤架上爬满了五叶藤萝,阳台都用玻璃包起来,却依然走风漏气。
只有那个僻静处的花园还收拾得十分漂亮,到了夏天,草坪碧绿,灌木整齐,球场外面围着修剪齐楚的岑树。房子另一侧有个果园,再远一点,能看到四个红色屋顶,那是仓库、马厩、牛栏等,里面养着四十匹马,六十头牛。在那之外,种甜菜的肥沃土壤一直伸展到遥远的地平线上,除此之外什么其他东西也没有。
“我这个选择还不坏,”玛妮娅一边关上窗户,一边自忖,“工厂的确不好看。不过也还是有益处的,有了它,这个小地方才比其他地方富庶,时常有人从华沙来,也时常有人到华沙去。糖厂有不少工程师和管理人员,这是桩不错的事情,可以上他们那儿借书看书。佐太太脾气不好,可她不是个坏女人。她并不把我当成家庭教师对待,因为她本人也一度当过家庭教师,她的好运到来得太快了些。她丈夫是个迷人的男人,她的大女儿简直是个天使,她的其他孩子也都不至于让人无法忍受。我看我算是非常走运了。”
这间屋子的一面墙壁,从上到下几乎让一个巨大而光滑的瓷壁炉占满了。玛妮娅烤了烤手,然后回到书桌前接着写信。她一直写到外面传来雇主专横的叫声:“玛丽亚小姐!”声音穿过墙壁和门扇,传进她的屋里。主人是在叫她去作陪伴呢。
孤身一人的家庭女教师都会写许多信,也希望收到回信,通报城里的消息。随着日月流逝,玛妮娅定时写信给自己的亲人,讲述自己生活中的种种活动,她要履行卑微的任务,也要一连几个钟头给人“作陪伴”,从工作中也能得到不少乐趣。她写信给父亲、给约瑟夫、给海拉、给她亲爱的布罗妮娅、给她中学时的朋友卡齐娅·普希波罗夫斯卡。她也写信给表姐亨利埃塔。这位表姐如今结婚了,住在利沃夫,可她仍是个激烈的“实证主义者”。玛妮娅坦率地把自己的心里话写信讲给表姐听,说出自己严肃的思考,自己的沮丧心情和希望。
一八八六年四月五日,玛妮娅给亨利埃塔的信上有这样的内容:
我按照自己职业的本分生活着。我给学生教课,自己也读一点书,不过并不容易找到时间,因为总有新来的客人打扰我,扰乱我利用自己的正常时间。有时候,这种情形让我非常恼火,我的学生安齐娅最喜欢找各种机会不上课,过后又很难让她恢复秩序。今天,我们又遇上麻烦了,她不按时起床。最后我不得不绷着脸拉着她的手把她从床上拖起来。我心里气得直冒火。你想象不出这种小事让我多么难过,有时候我一连几个钟头不开心。不过我总得制服她才行。
……你问我作陪的时候谈什么话题?除了闲扯还是闲扯,什么张家长李家短啦、舞会啦、聚会啦等等。要说跳舞,这地方的年轻姑娘舞跳得真是尽善尽美,恐怕哪儿都找不着这么好的舞蹈高手。从这一点上讲,她们还算不坏,有些人也很聪明,但是她们没接受过多少教育,智力没有得到开发。当地人又特别喜欢一场接一场组织荒唐的宴会,把她们仅有的一点点智力也消耗光了。这里有点脑筋的好小伙子实在太少……不论是姑娘还是小伙子,“实证主义”或“劳工问题”之类话题,他们听都不愿听,这种情况实在少见。相对来说,佐先生家还算比较有教养。佐先生是个老派人物,但是也有很好的见识,他富有同情心,也讲道理。他妻子是个难以相处的人,不过只要习惯了,她还是个挺好的人。我认为她还是挺喜欢我的。
你真该看看我在这里的模范行为才对!我每个星期天和节日都去教堂做礼拜,从不借口头痛或感冒而缺席。我几乎没有谈到过妇女接受高等教育问题。在任何情况下,我都恪尽职守,遵循我的本分礼数。
复活节我要回华沙去度几天假。一想到这个,我的心里就乐开了花,简直要跳起来了……
玛妮娅描述自己的“模范行为”不无讥讽口吻,她骨子里有一种大胆的独创性格,无法长期忍受墨守成规的生活。她内心中一直是个“实证主义者”,渴望成为有用的人,渴望参加斗争。
一天,她在泥泞道路上遇到几位衣衫褴褛的姑娘小伙,见到这几位年轻农夫亚麻色头发下的愚顽面孔,她心里忽然有了个计划。自己有宝贵的进步思想,干吗不在斯茨组基这个小天地里付诸实施呢?前一年,她还梦想过要“为人民启蒙”呢。现在就是个极好的机会。村子里的孩子们大半是文盲。就是偶尔上过学的,也只学会点俄语字母。要是能秘密教他们波兰语,唤醒这些年轻的人们,让他们认识到祖国语言有多美、历史有多悠久,那该多好!
我们这位家庭教师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佐小姐,佐小姐立刻表示赞成,而且决定帮助她。
“再仔细想想吧,”玛妮娅想让她冷静下来,“你知道的,要是有人告发,我们就会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去。”
但是,勇气比任何东西都更有感染力,玛妮娅从布朗卡·佐小姐的眼睛里看到的是热情与坚定。只要得到家长的允许,她们就能在那些农夫的小屋里谨慎地搞宣传了。
一八八六年九月三日,玛妮娅在写给亨利埃塔的信中说:
……今年夏天我有个假期,可我不知道该上哪儿去,于是就待在斯茨组基。我并想花钱去喀尔巴阡山。我每天给安齐娅教好几个钟头的课,陪布朗卡读书,还给这里一个工人的儿子讲一小时课,为他进学校做准备。除此之外,布朗卡和我还一天给几个农夫的孩子们讲两个钟头的课。有十个孩子听课,其实算作一个班了。他们倒是愿意学习,可我们的任务还是十分艰难。后来他们的学习成绩渐渐有了进步,而且相当快,这让我感到安慰。因此,我每天都很忙。除此之外,我还要自学一点东西,有时要独自学很多东西……
一八八六年十二月,玛妮娅在写给亨利埃塔的信中这么说:
我教的农民学生人数增加到十八人。他们当然不能同时来上课,我无法应付那么大的班。不过,他们每天要学习两个钟头。星期三和星期六,我教他们的时间略长些——长达连续五小时。幸亏我的房间在二层楼,有单独的楼梯通向院子,因此,这一工作并不影响我对佐家的义务,也不影响其他人。这些孩子们让我获得了极大的愉快,也得到了极大的安慰……
这样一来,玛妮娅要听安齐娅喃喃地背课文,要辅导布朗卡做功课,遇上朱列克从华沙回来,要监督他做作业,除此之外,这位不屈不挠的姑娘还要回到自己房间里等着教那批农民学生,听到楼梯上响起靴子和赤足踏出的声音,她知道自己的学生们要到了。她借来一张松木桌子和几把椅子,好让他们舒舒服服坐下来写字。她还从自己的积蓄中拿出不少钱,为他们购买抄本和钢笔,学生们就用不听使唤的手指吃力地书写。在这间石灰墙的大房间里,如果来了七八位小农民学生,维持秩序和帮助差等生就够玛妮娅和布朗卡·佐费劲了。那些差等生急得又抽鼻子又喘粗气,就是拼写不出难记的单词来。
围在玛妮娅周围的这些金发孩子,父母都是做仆人、农民、工厂工人等工作的,他们身上的深色衣服不常清洗,从来气味不佳。有的孩子不用心学习,显得闷闷不乐。不过,大多数明亮的眼睛里都流露出一种天真的热切愿望,希望将来有一天拥有能读会写的神奇本事。这种卑微的目标实现后,白纸上的大黑字对他们忽然有了意义,孩子们不禁为自己的胜利得意欢呼,就连偶尔坐在屋子另一头旁听的文盲家长也赞叹不已。每逢听到这种声音,我们这位年轻姑娘的心会激动得不能自已。她不禁感叹,不知有多少求知的愿望落空了,也不知道大批不为人知的人群中蕴藏着多少天才。面对这片愚昧的海洋,她觉得自己太软弱、太无能为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