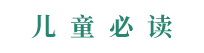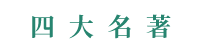第九章 每月四十卢布
不错,玛丽的生活还没有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她在德意志路上那所房子里度过了一个新环境适应期。如今这位姑娘慢慢开始独自生活了。在她眼里,与她擦肩而过的人似乎并不存在,仿佛他们不过是路上蹭到的墙壁,难得有什么谈话声能打进她心灵的沉寂。未来三年多时间里,她要独自投身学问,这正符合她梦想中的生活,这是一种与隐士和修士无异的“完美”生活。
她的生活也不得不像修道士那样简朴。自从玛丽自愿放弃德卢斯基夫妇提供的食宿后,她就得自行支付所有费用。她将自己的积蓄加上父亲给她寄的一小笔款子仔细分配,她的预算是每月四十卢布。
当时是一八九二年,一个住在巴黎的外国女子,怎么能靠这么一丁点钱过体面的生活呢?要知道,那笔钱只能合每天三个法郎,她还得靠这点钱付房租、应付三餐、购买必要的衣物、纸张和书籍,更别提还得支付大学的费用。这是这位年轻的学生亟须解决的问题。但是,玛丽从来没有发现有什么问题是不能解决的。
一八九二年三月十七日,玛妮娅在写给哥哥约瑟夫的信中说道:
你大概已经从父亲处得知,我决定搬到离学校比较近的地方住,我不得不这么做有几条理由,首先是出于本学期的考虑。这个计划已经实现了。我现在就是在新住址给你写信,地址在弗拉特路三号。屋子很小,不过房租十分低廉,而且非常合适。从这里只要走一刻钟就能到化学实验室,二十分钟就能走到巴黎大学。当然,没有德卢斯基夫妇的帮助,我绝对没有能力安排这一切。
我如今学习用功超过刚来时的一千倍。在德意志路上那所房子里,姐夫总是不停地打扰我。他绝对不能容我闲着没事,只要我回到家,他就要我陪他聊天解闷。为此我被迫跟他吵了一架。几天后,布罗妮娅和他觉得不好意思,来看我。我们一道喝茶,双方和解了。然后我们下楼去看望邻居,就是姓斯的朋友一家。
你妻子答应我要照顾父亲的,她做得怎么样?让她照顾吧,反正都一样,不过别让她把我在家里的地位完全夺走!父亲谈到她已经变得十分亲切了,我恐怕他不久便会把我忘掉……
照玛丽这样住在拉丁区每月只花一百法郎的学生不止她一个。大多数波兰同学都像她一样贫穷。他们有些是三四个住在一起,有些是独自生活,每天花费几个钟头收拾屋子、做饭、缝补衣服,凭自己的精明能吃饱肚子穿暖身子,有的衣着讲究些,有的随便些。布罗妮娅初来法国时也采用类似方式,她的烹饪本领在同学中间是十分有名的。
玛丽不屑于因循这种榜样。她太喜爱独处了,不愿与任何朋友合住。她学习太专心,根本不在乎自己的生活是否舒适。不过,就算她有意搞得舒适一些,也无能为力。这位姑娘自从十七岁就在别人家里当家庭教师,每天教课七八个钟头,在学习料理家务方面既没有时间也没有机会。布罗妮娅在帮助父亲料理家务方面学到的东西,玛丽根本不懂。于是,波兰侨民中间有一种传闻,说是“斯科洛多斯卡小姐不知道汤是用什么做的。”
她既不知道,也不愿去了解。她哪里舍得花费一个上午时间,去掌握做汤的秘诀呢?她宁愿花费这么长的时间读几页物理学,或者在实验室做一个有意义的分析。
她刻意将分心的事情从自己的日程表中排除掉,既不参加朋友间的聚会,也不与任何人接触。同样地,她认为物质生活并不重要,甚至觉得物质生活并不存在。根据她的原则,她为自己规定的是斯巴达式的生活(1),几乎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
弗拉特路、波特罗亚尔大道、弗扬替纳路……玛丽后来在这些地方住过的屋子都是一样的不舒适,不过租金都很便宜。第一处是在一个有简单家具的房子里,租户都是学生、医生、附近军营的军官。后来,这位姑娘为了追求绝对安静,就在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的房子里租用了一个阁楼,房间就像佣人的住房。她花费每月十五法郎或二十法郎便租下这种极小的屋子,倾斜的屋顶上有个小窗户透进光线,从这种枪眼似的小窗,能看见一方天空。屋子里没有供热,没有照明,没有供水。
玛丽用她拥有的一切物品布置这个地方:一张铁折叠床,上面铺上她从波兰带来的床垫、一个炉子、一张白色木桌子、一把厨房椅子、一个洗脸盆、一盏煤油灯,上面罩着两个苏(2)买来的灯罩、一个从楼梯口水龙头打水的桶、一个只有碟子大小的酒精炉,以后三年中,她一直用这只炉子做饭。她有两个盘子、一把刀、一把叉子、一把勺子、一个杯子、一个平底锅,此外还有一个茶壶和三只玻璃杯,德卢斯基夫妇来看望她的时候,她就按照波兰风俗用这三只玻璃杯奉茶。遇上有客人来访,她待客十分殷勤,不过客人来访的情况极其罕有。这位姑娘会生起小火炉,让烟从蜿蜒曲折的烟筒里冒出去,她还会拉出屋角那只棕色大木箱当座位。这木箱既是她的衣橱,又是她的衣柜。
她当然不要人为她服务,每天一小时的清洁费用便远远超出了她的预算。交通费用也省掉了,玛丽不论天气好坏都步行去巴黎大学。煤的消耗量控制在最低水平,她每年冬天仅仅使用一两袋煤块,是从街角的店铺里买来,自己一桶一桶沿着陡峭的楼梯一直提到七层楼,每登上一层楼,她都要停下脚步喘喘气。她的照明花费也很少,天一黑,这位学生就到圣日内维埃图书馆去,那是个幸福的避难所,里面有明亮的煤气灯,而且相当暖和。这位可怜的波兰姑娘会在那里双手捧住脑袋一直用功到十点钟关门。这以后,就需要她在自己屋子里点煤油灯照明看书,一直到凌晨两点钟。最后,玛丽疲倦得两眼都红了,这才不得不放下书本,倒在床上睡觉。
在卑微的实践技能方面,她只会做一件活计,那就是缝纫,这是西科尔斯卡寄宿学校“女红”课留下的纪念,也是在斯茨组基当家庭教师的漫长日子里留下的纪念,当初这位家庭教师一边督促孩子做功课,一边做着缝纫活计……我们不能轻率地假定,这位流亡者会偶尔买块廉价布料,自己动手做件新衬衫来穿。正相反,她似乎发誓要永远身穿从华沙带来的衣服,尽管这些衣服已经破旧不堪,也决不放弃。她总是注意保护自己的衣服,遇到学习太疲惫了,就动手在洗脸盆里洗衣服,还要缝补完整。
玛丽不承认自己会感到冷,也不承认自己肚子饿。为了节省买煤的钱,有时候也是由于根本不去留意,她常常忘记在烟筒弯曲的小火炉里生起火,结果,在写下一串串数字和一道道方程式的时候,往往感觉不到自己的手指已经冻僵,也留意不到两个肩膀在颤抖。要是能喝一碗热汤,吃一点肉,她会感到舒服得多,可玛丽连汤也不会做,更舍不得花费一个法郎外加半个钟头时间去烧排骨。她很难得走进肉店,更不用说下饭馆吃饭了,毕竟价格太昂贵。一连几个星期,她只吃涂着黄油的面包,喝的只有茶。她想吃点像样的东西,就去拉丁区一家小饭店吃两只鸡蛋,或者买一块巧克力或一点水果。
靠这种饮食维生,几个月前离开华沙时身体结实的姑娘很快便患上了贫血。她常常从书桌旁站起身时觉得脑袋晕眩,紧赶几步倒在床上,立刻就失去了知觉。苏醒过来后,她就问自己怎么会晕倒,心里觉得可能自己得了病,但是又会像蔑视一切那样,蔑视自己的疾病。她从来没想过,自己的唯一疾病是营养不良导致的虚弱。
她自然还要对德卢斯基夫妇夸口,说自己的生活安排无与伦比。每次她去看望他们,他们问起她的烹饪手艺是否有进步,问她每天吃些什么,她的回答总是扼要的一两个字。要是她姐夫说她气色不佳,她就说那是因为学习用功的缘故,事实上,她也真的认为这是她身体疲惫的原因。然后,她会作一个手势,让大家别考虑这种生活琐事,继续与她的外甥女玩耍。她非常喜爱布罗妮娅的女儿。
有一天,玛丽当着自己一位同学的面晕倒了。那位同学慌忙跑到德意志路去找两位年轻的大夫。两小时后,卡什米尔奔上七层楼,来到姑娘住的阁楼上,只见这位姑娘已经不顾面色苍白,开始学习第二天的课程了。她为妻子的妹妹检查了身体,也仔细查看了她空空如也的盘子和平底锅,在整个屋子里,他只找到一种可下肚的东西:一小包茶叶。他立刻明白了,开始盘问。
“你今天吃过什么东西?”
“今天?我不记得了。我刚刚吃过午饭。”
“午饭吃的是什么?”卡什米尔不肯就此罢休,继续追问道。
“有樱桃,还有……还有各种其他东西。”
最后玛丽不得不说实话,自从昨天晚上起,她只吃过几根小红萝卜,还有半磅樱桃。她一直学习到凌晨三点钟,睡了四个钟头,然后就去大学了。回来后,她吃完那几根小红萝卜。然后就晕倒了。
这位大夫没多说话,他气坏了。他生玛丽的气,玛丽那双灰色的眼睛看着他,带着深深的倦意和天真神色。他也深深自责,埋怨自己对这个“小东西”不够关心,他曾向斯科洛多斯基先生保证说要照顾好她的。他不顾小姨子一再抗议,把她的外套和帽子递给她,要她带上下一个星期用的书籍和笔记本,然后沉下脸,不由分说带她到了拉维里特路的家里。来到家门口,他大声叫布罗妮娅,布罗妮娅连忙奔向厨房。
二十分钟过后,玛丽便一口口吞咽着卡什米尔大夫为她开的药:一大块夹生牛肉、一盘酥脆油炸土豆。她的脸上奇迹般出现了血色。当天晚上,布罗妮娅亲自来到为妹妹准备好床铺的屋子里,在十一点钟为她熄了灯。在几天时间里,玛丽吃得很好,受到良好的照顾,接受了“治疗”后,又恢复了体力。接着,她心里牵挂着即将到来的考试,保证说以后一定要懂道理,便返回她的阁楼。
但是,第二天她又开始靠喝西北风过日子。
学习……学习!玛丽全身心投入学习,为自己取得的进步如痴如醉,觉得自己能掌握人类业已发现的一切知识。她上数学、物理、化学课,一点点熟练掌握了科学实验的技术和细致的手法。不久李普曼教授交给她一些研究工作去做,虽然这些研究并不非常重要,只是给她个表现思维敏捷和独创性的机会,可她却感到十分喜悦。巴黎大学的物理实验室是一间又高又宽大的房间,有两道奇特的螺旋楼梯通往里面的一个走廊。玛丽·斯科洛多斯卡就在这里谨慎地一试身手。
她热爱那种专注而宁静的气氛,热爱实验室的环境,直到她生命的最后一天,她喜爱这种环境都胜过喜爱任何其他地方。她站着工作,从来都是站着工作,站在摆放精密仪器的橡木桌子前,或者站在化学实验的通风罩前,照料着烧杯里猛烈冒着泡进行的反应。她身穿一件皱巴巴的肥大工作服,与旁边沉思的年轻人没有区别,大家都仔细注意着眼前的烧杯和仪器。她也像大家一样,尊重这里专心的气氛,不弄出响声,不说一句废话。
一个学士学位不够,玛丽决心要拿两个学位:一个物理学学士学位,一个数学学士学位。她以前订的计划要求很低,如今要求迅速膨胀起来,速度快得让她没时间向斯科洛多斯基先生透露,也没胆量对父亲这么说。她心里清楚,父亲正焦急地等待着她,等她返回波兰。这位好先生一如既往地向她提供帮助。但是,老人显然朦胧地感到担忧,自己孵化的小鸟羽翼渐丰,在多年的服从和牺牲之后,如今具有了独立性,要振翅高飞了。
一八九三年三月五日,斯科洛多斯基先生在写给布罗妮娅的信中说道:
……你上次信中首次谈到玛妮娅打算参加学士学位考试。虽然我问过她,可她在给我的信中对这事绝口不提。写信告诉我,这些考试何时举行,玛妮娅希望什么时候通过考试,考试需要多少费用,得到文凭需要多少钱。我必须事先作通盘考虑,便于给玛妮娅寄钱,我个人也要以此为基础做出计划。
……我打算把现在住的房子再保留一年,供我自己和玛妮娅居住,如果她回来,这所房子非常合适……玛妮娅可以慢慢招募一些学生,无论如何我都愿意与她分享自己拥有的东西。我们可以把事情安排好,并不费事的……
无论玛丽如何胆怯,每天都不可能不见到人。有些人对她十分热心友好。在巴黎大学,人们对外国女性十分重视。这些外国女子尽管贫穷,但一般都富有天分,她们从遥远的地方来到这所大学,往往能激起法国青年的同情。巴黎大学曾被龚尔古兄弟(3)称作“学问的奶妈”。这位波兰姑娘受到了吸引。她发现自己“铁杵磨针”的同学都尊重她,而且希望与她亲近,有时甚至可能变得过分亲近。玛丽一定非常美丽。她的朋友迪丁斯卡小姐是一位迷人而特别热心的女子,她自封为玛丽的保镖,一天甚至挥动雨伞,威胁要对一群过分殷勤的崇拜者动粗。
这位年轻姑娘一方面任凭迪丁斯卡小姐赶跑那些她并不感兴趣的人们,另一方面却接近那些并不向她献殷勤的人们,与他们谈学习中的问题。在一堂物理课与实验的间歇时间,她同保罗·潘勒维教授闲谈,同未来法国科学界的先驱人物查尔斯·莫林和让·佩韩交谈。这种关系谈不上交情,玛丽没有时间结交朋友,没有时间谈情说爱。她爱的是数学和物理学。
她的头脑太精确,思路太清晰,斯拉夫式的混乱休想破坏她的努力。她有着铁一般的意志,有着追求完美的疯狂品味,也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坚毅。凭着自己的耐心和执著,她一步步实现了自己的目标:首先,她在一八九三年得到了物理学学士学位,后来又在一八九四获得了数学学士学位。
她决心把法语学到完美境界,因为这是她绝对不可或缺的语言。许多波兰人在法国生活了许多年,仍然只能结结巴巴用单调的句子说话,她却极其认真地学习拼写和句法,使句子无可挑剔,并尽力改正自己的地方音。后来,她的发音中只有那个小舌音仍然稍有些不纯正,不过听起来十分婉转柔和。
她靠每月四十卢布成功地维持了生活,有时不得不从必不可免的费用中设法节省,不过有时候也能获得某种奢侈:时而晚上出去听一场歌剧,有时到郊外散散步,还能从树林里采摘到鲜花带回来,让她的桌子上一连几天熠熠生辉。她原先有过的农民气质并未消失,如今身处这个大城市中,她仍留意着树木是否萌出新绿,只要有一点点时间和余钱,她就匆匆赶到树林里去。
一八九三年四月十六日,玛丽在写给斯科洛多斯基先生的信中说:
上个星期日,我去了巴黎附近的兰西,这是个漂亮宜人的近郊。那里的丁香和果树都开了花,就连苹果树也盛开着花儿,空气中飘满了花香。
在巴黎,四月初树就绿了。现在树枝都已抽出新绿,栗子树也开花了。天气热得像是夏天,到处一片绿油油。我的屋里已经开始燥热。幸而到了七月份备考的时候,我就不在这儿住了,因为这间屋子的租期七月八日终止。
考试越临近,我就越觉得准备不够。万一发生最糟糕的情况,我就得等到十一月复考,要是那样的话,我就得损失一个夏天,我可不愿发生那种情况。考试情况如何,到时候再看吧……
七月来临。那是个折磨人的早晨,三十位同学关在一个考场里,大家焦急、难受、遭受磨难。玛丽精神极度紧张,考题上的字在她眼前乱跳,在这份决定命运的考卷上,她甚至读不懂题意,读不懂什么是“课程命题”。考试结束后,接着是一连几天的等待,最后公布成绩的庄严时刻到来了。玛丽与竞考者们(4)及其家长一起挤在那间阶梯教室中。竞争成功者的名单要在这里按照成绩高低先后宣布。大家互相推挤着,喧哗着,等待考官入场。忽然全场一片肃静。她听见自己的名字第一个宣读出来:玛丽·斯科洛多斯卡。
谁也猜不到她此时情绪有多激动。她从同学们的祝贺声中脱出身来,跑得远远的。假期开始,她该回波兰老家了。
波兰穷人回家是有规矩的,玛丽严格遵守着这种规矩。她把自己的床、火炉和厨具都存放在一个同胞那里,这位波兰人还有足够的钱在夏天的几个月里保留自己租的房间。她退掉自己租的阁楼,离开前把屋子彻底打扫了一遍。她向门房的女佣道别,买了些打算在路途上吃的食物,她计算过自己剩下的钱,然后走进一家大商店,做了一桩一年来从未做过的事:买几件小摆设和围巾……
回国时口袋里还带着当地的钱是丢人的。不论是按照流行时尚,依从风俗,还是出于保持风度的考虑,都应该在巴黎北站上车之前把钱花个干净,把所剩的钱全都用在给家人购买礼物。这么做不是很聪明吗?两千公里之外,在铁路的另一端,有斯科洛多斯基先生、约瑟夫和海拉,有熟悉的家,有吃不尽的食物,还有裁缝,只要花几个格罗兹,就能裁剪缝制衬衫和厚厚的毛料外套。玛丽十一月份回到巴黎大学时,就可以身穿这些衣服。
等她回到巴黎大学时,会显得神情欢乐,身体丰腴。斯科洛多斯基家在波兰的亲戚都不喜欢看到她气色不佳,在这三个月里,亲戚们都会请客,把她喂得饱饱的。然后她又要去度过一个学年,又要刻苦学习,为考试做准备,会再次变得消瘦。
但是,每逢秋季来临,玛丽必然产生同样的忧虑:她怎么才能返回巴黎?她的钱上哪儿去筹集?每个月花费四十卢布,她的积蓄已经枯竭了。一想到父亲为了帮助她,自己连一点小小的享乐都放弃了,她便觉得羞愧。在一八九三年,她感到绝望,几乎打算放弃旅行了。就在这时,一个奇迹出现了。去年,迪丁斯卡小姐曾操起雨伞保护她,如今,这位迪丁斯卡小姐又一次出面保护她。她确信玛丽必然有了不起的前途,便在华沙上下活动,为玛丽申请“亚历山大奖学金”。这种奖金是为成绩优秀的学生在国外深造而设。
她得到六百卢布!足够靠它生活十五个月了!玛丽懂得如何为别人求助,却从来没有想过为自己的事向人咨询,更没有勇气提出必要的申请了。她大喜过望,立刻赶往法国。
一八九三年九月十五日,玛丽从巴黎写信给哥哥约瑟夫说:
……我已经租到了房间,屋子在七层楼,外面的街道清洁而雅致,房子很适合我。请告诉父亲,我原先打算租的房子很不方便,这间屋子我觉得非常满意。屋子里有一扇能关得很紧的窗户,等我把一切都安顿好了,冬天不会冷,特别是屋里有木地板,而不是砖地。与我去年租的房子相比,这儿简直是座宫殿。租价是一年一百八十法郎,比父亲跟我说的那一处便宜六十法郎。
我用不着说你也知道,我回到巴黎觉得很高兴。再次离开父亲让我难过,不过我很高兴看到他身体健康,精力旺盛,没有我也过得很好。尤其是你们都住在华沙。我打算拿我的整个生命做赌注,因此我觉得留在这里不必感到内疚。
我目前在毫不间断地研究数学,为的是等课程开始能赶上进度。我每周三次与一位法国同学一道讨论我通过的考试内容。请告诉父亲,我已经习惯了这种学习生活,不像以前那样感到疲惫了,我也不愿放弃这种生活。
今天我开始布置这个学年要住的这个小角落——虽然十分寒碜,不过有什么办法呢?我不得不自己动手做一切事情,要不然就太昂贵了。我必须把家具都摆好,我把这些东西叫做家具其实太夸张了,其实合在一起还不值二十法郎呢。
我要尽快给约瑟夫·博古斯基写封信,请他介绍实验室的情况。这关系到我未来的工作。
一八九四年三月十八日,玛丽在写给她哥哥的信中说:
……我很难把自己生活中的详细情况描述给你听,因为生活十分单调,而且实际上没什么乐趣可言。不过,我并不觉得单调,让我遗憾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日子太短,时光太快,永远也看不出取得了什么进展,只能看出还应该做什么。要是不喜欢自己的工作,真能让人失去勇气。
我希望你的博士论文能够通过……看来,我们谁的生活都不容易。可这又有什么关系?我们必须坚定不移,最重要的是要对自己有信心。我们必须相信,自己在某种领域有天分,不论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都必须实现自己的目标。也许一切到头来都会有好的结果,尽管此时我们似乎觉得希望渺茫……
她能获得亚历山大奖学金实在幸运。玛丽刻意节俭,设法让这六百卢布多用些时日,好在演讲厅和实验室的天堂中尽量多留一段时间。几年之后,全国工业促进协会请她进行一项技术研究,她以同样的刻意节俭风格,从自己的第一次收入中省出六百卢布,送到亚历山大奖学金委员会,交给那里的秘书,这位秘书惊呆了。该委员会的历史中从来没有送还奖学金的记录。玛丽接受这笔奖学金的时候,把这笔钱视作对她的信任,视为一种信用贷款。在她不屈的灵魂中,她认为这笔钱在自己手里多留片刻,都是一种不诚实的行为,因为对于另外一个贫寒的青年女子,这笔钱可能是个救生圈。
每当重读我母亲就她这段生活用波兰文写的一首散文诗,追忆她昔日有时面带微笑说出的幽默话语,看着她自己喜爱的唯一照片:一个女学生目光坚定、下巴坚毅的一幅小照片,我便始终感到,她喜欢这些艰苦奋斗的岁月远远胜过别的生活方式。
啊,学生时代过得多么艰苦顽强,
她周围的青年个个热情而欢乐
其他青年渴望寻找轻松的愉快!
可是,在孤独中
她过着默默无闻却无比幸福的日月,
她在自己的陋室中找到了热诚
使她的心胸变得无比宽广。
这幸福的时光已经消逝,
她必须离开科学的领地
到外面为衣食奔忙
踏上生活的灰色路途。
她疲惫的精神一再一再
返回那些屋顶下面
回到她永远感到亲切的角落
那里有过苦苦的无声奋斗
那里还留着记忆的宝藏。
毫无疑问,玛丽后来也有过其他欢乐。然而,即使是在她爱意绵绵的时刻,即使是在她成功和享誉的时刻,这位永远孜孜不倦的学生,从来没有像哪位穷学生苦苦奋斗时一样对自己感到满足,感到骄傲。她为自己的贫穷感到骄傲,为自己独自生活在外国的一个城市里感到自豪。当时她在可怜的小屋里灯下苦读,觉得自己的命运十分渺小,却仿佛与某种她敬仰的高尚生活神秘地联系在一起,仿佛将成为昔日伟大科学家卑微的同伴。那些人也曾像她一样,躲在光线黯淡的小屋里,像她一样逃离自己的时代,也像她一样鞭策自己的才智,超越业已为人类掌握的知识领域。
不错,这英雄般的四年并不是玛丽·居里生活中最幸福的时光,然而,在她眼睛里,这四年却是最完美的一段时光,最接近她仰望的顶峰,她认为自己的使命便是利用得到的训练抵达那个顶峰。一个年轻而孤独的人完全沉醉在学习中,尽管“生活无着”,却在过着最充实的生活。一种强烈的激情使这位二十六岁的姑娘获得了极大的力量,让她无视经受的磨难和贫困,将卑微的生活化为神奇。后来,恋爱结婚,生养孩子,承受做妻子当母亲的忧伤,从事繁杂而令人心碎的艰苦工作,这些要让一个幻想家恢复真实的生活。但是,在那些让她着魔的时刻中,虽然她比以后任何时期都穷苦,可她却像个孩子一样无忧无虑。她是在另外一个世界中轻松翱翔,她永远认为那才是唯一纯洁而真实的世界。
在那样的冒险生活中,不可能天天都是好日子。常常会发生意外事故,突然打乱一切,而且无法补救:无法克服的疲惫,不得不治疗的短期疾病。还有其他令人恐惧的灾难:唯一的鞋子鞋底磨穿几个洞,最后彻底不能再穿,不得不买双新鞋。这就意味着把几个星期的预算彻底打乱了,这笔巨大的开销不得不从多方面弥补,从食物中节省,从灯油中节省。
遇上冬季比往年漫长,七层上的阁楼里一片冰冷,冷得让玛丽无法入睡,冷得她浑身发抖,牙齿打战。而她的煤已经用光……可这又算得了什么?难道一个波兰姑娘能向巴黎的严冬屈服?玛丽重新点上煤油灯,看看四周,打开大木箱,把自己的所有衣服都拿出来,能穿的衣服都穿在身上,然后再钻进被窝里,把其余衣服和衬衫都盖在薄薄的被子上,可她还是觉得太冷。玛丽伸手把唯一的椅子拖过来,干脆也压在被子上面,让自己有一种重量和热量的感觉。
现在她只能静静等待睡意来临,因为她已经成了上面这个架子的活基础,为了保持架子不倒,她不能移动。与此同时,水桶里慢慢结了一层冰。
————————————————————
(1) 斯巴达式的生活:古希腊城邦斯巴达的生活方式,以简朴刻苦著称。
(2) 苏:法国旧币辅币名,二十苏等于一法郎。
(3) 龚尔古兄弟:指法国自然主义小说作家爱德蒙·龚尔古和于勒·龚尔古(Edmond Louis Antoine de Goncourt 1822—1896, Jules Alfred Huot de Goncourt 1830—1870)。
(4) 竞考者们:巴黎公社革命之后,法国大学不收学费,高中毕业生可随意入学,但每年考试不合格便被淘汰。因此考试就是竞争下一学年继续学习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