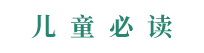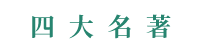第十四章 艰苦的生活
如果皮埃尔和玛丽能将全部精力放在那间简陋的实验室,全身心投入与自然的奋斗,那他们准会感到非常幸福。
可惜他们还得为其他事情操心,那些事情他们做得并不都很成功。
皮埃尔为了一个月五百法郎的工资,每月授课一百二十小时,还要指导学生做实验。做完这种令人筋疲力尽的工作,他才能抽出时间和精力从事研究。居里夫妇没有孩子的时候,玛丽能独自应付家务劳动,五百法郎供两夫妇使用还是足够的。但是,艾莱娜出生后,雇女佣和奶妈花去他们预算的很大一部分。他们不得不寻找新的收入来源,首先是皮埃尔外出寻找,接着玛丽也出动了。
这是两个优秀人物,因为每年缺少两三千法郎,却不得不厚着脸皮东奔西走。没有比这更让人感到沮丧的事了。问题还不仅仅是搞一种副业弥补收入的不足。我们知道,皮埃尔·居里把科学研究看做头等大事,宁肯不吃饭不睡觉也不能不去那间棚屋实验室工作。然而,他在学校的工作占去了他的大部分时间。他其实不该另搞副业,而应该减轻工作负担才对。可他们需要钱,又该怎么办呢?
其实办法非常简单。皮埃尔显然能够胜任在巴黎大学任教,只要能在那里担任教授,不但能得到每年一万法郎的收入,而且比物理学校的课时负担轻得多。他的科学知识能让学生受益,也能提高大学的声望。如果担任大学教授还有使用一个实验室的便利,皮埃尔对命运的要求便全部得到满足了。他卑微的要求无非是下面这些:得到一个赖以维生的教授职位,教授他的物理系学生;有个工作用的实验室。这个实验室应该具有那个棚屋没有的东西:供电和技术设备,有助手用的办公室,冬天要有点暖气……
这简直是疯狂的要求,是狂妄的梦想!直到全世界都承认了他的价值,他才在一九〇四年得到教授职位。而他需要的实验室却根本没有得到。死神比政府官员更敏捷,抢先夺走了伟大人物的生命。
皮埃尔揭开神秘现象时手段高明,也有解开物质谜团的天赋,但是,在谋求职位方面却愚钝不堪。他最大的弱点就是富有天才,这最能在竞争对手心里激起无法调和的嫉妒。他根本不懂得搞阴谋耍手腕。他最合法的资格对自己毫无用处,因为他并不懂得如何利用。
后来,亨利·普安加瑞在写到他的时候曾有这么一段话:
他随时准备谦让,在朋友面前如此,甚至在对手面前也是如此。他是人们说的那种“笨拙的候选人”。但是,在我们的民主国家里,候选人从来不缺乏。
一八九八年,巴黎大学有个物理化学专业的职位空缺,皮埃尔·居里决定申请这个职位。公平地说,对他的提名应该得到确认。但是,他没有上过师范学校,也没有上过理工学院,因此没有这些院校对毕业生的决定性支持。此外,某些吹毛求疵的教授表示说,他过去十五年宣布的各种发现,“严格地说”并不属于物理化学范围……他的申请遭到了否决。
弗里德尔教授是一位支持他的人,这位教授写信对他说:
我们失败了。我鼓励你提出申请却遭受了失败。但是讨论过程比表决对你有利得多,要不是这样,我就只剩下遗憾了。虽然李普曼、布提、伯拉和我都做出了努力,尽管反对你的人也赞扬你取得的非凡成就,但是,面对一个师范出身的人和一群数学家的偏见,又有什么办法呢?
“讨论过程对皮埃尔有利”,这总算是个心理补偿。未来几个月不可能有报酬丰厚的职位,居里夫妇在聚精会神从事研究镭的伟大工作,他们宁愿勉强度日,也不愿把时间浪费在找工作的接待室里。他们继续做着可怜的工作,却并不抱怨。毕竟,五百法郎还不算极度贫穷。生活还是能过,只是十分艰难而已。
一八九九年三月十九日,玛丽在写给约瑟夫·斯科洛多斯基的信中说:
我们不得不精打细算。我丈夫的工资不够生活所需,但是,我们每年都能得到几笔额外收入,因此还没有负债。
不管怎么说,我希望我和我丈夫不久便能找到稳定的工作。到时候,我们不但生活无忧,而且还能为我们孩子的未来积攒一点钱。我希望先通过博士学位考试,然后再找工作。目前,我们研究新金属元素的工作太忙,我无法为博士学位考试做准备。不错,我的博士学位是以这项研究为基础的,不过通过博士学位考试要求做额外的研究,可我现在根本没时间搞那些研究。
我们的身体很好。我丈夫的风湿病不太要紧,因为他每天都喝牛奶、鸡蛋和蔬菜,他不喝酒,不吃瘦肉,每天喝很多水。我身体很好,从来不咳嗽,体检和痰检都证明,我的肺毫无问题。
艾莱娜发育正常。她十八个月时断了奶,不过我当然要让她长时间喝牛奶。现在我给她喝牛奶,吃“母鸡刚下的新鲜鸡蛋!”
一九〇〇年……账簿上记载的支出在增加,超过了收入。现在老居里大夫与儿子住在一起,家里包括一名女佣共有五口人。玛丽在凯勒曼大道上租了所房子,好住得下五口人。这房子的租金是一千四百法郎。迫于生活压力,皮埃尔经过申请得到了理工学院的辅导教师职位。干这桩苦差事能让他每年挣得两千五百法郎。
忽然,他们意外得到了一个聘用建议,但这个建议并非来自法国。虽然大众还不知道他们发现了镭,但这一发现已经在物理学界传开了。日内瓦大学愿特聘该校认作欧洲一流的科学家夫妇。该校校长愿聘任皮埃尔·居里为物理学教授,年薪一万法郎,另有住房补贴,由他指导一个实验室,“与居里教授签约后可增加实验经费,并可指定两名助手。在实验室经费允许的情况下,可完善物理实验仪器的配置。”玛丽可在同一个实验室中得到一个正式职位。
命运专好作弄人,送来了人长期以来渴望的东西。然而由于一桩小小的差异,却让人无法接受。假如发信地址不是“瑞士日内瓦州”而是“巴黎大学”,居里夫妇会感到多么幸福啊。
日内瓦方面态度十分诚挚,给皮埃尔的聘约充满敬意,皮埃尔相当感动,便表示接受。到了七月,他和玛丽去了瑞士,受到同行的热情欢迎。但是,在度过夏天的过程中,他们心里产生了顾虑。难道他们不得不花费好几个月时间为适应重要的新教学工作做准备?难道因为设备运输困难,不得不中断提纯镭的工作?两个痴迷工作的科学家觉得无法忍受。
皮埃尔·居里叹息着给日内瓦发了一封信,表示谢忱,致以歉意,并辞去这一职务。他不顾舒适生活的诱惑,为了对镭的热爱,打定主意继续留在巴黎。到了十月份,为了得到更多额外收入,他放弃理工学院的辅导职位,接受了在巴黎大学理化自然科学学部的职务,地址在居维埃路上。玛丽也希望分担家庭重担,便向凡尔赛宫附近的赛弗尔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提出任教申请。该校副校长向她发来了聘书,内容如下:
夫人:
我荣幸地通知您,根据我的推荐,赛弗尔师范学校聘请您在一九〇〇至一九〇一学年度讲授一、二年级物理课程。
敬请自本月二十九日星期一起接受校方的授课安排。
由于这两次“成功”,他们家的经济在今后较长的一个时期稳定了下来。然而,在放射性实验需要大量投入精力的时候,他们的工作负担大大加重了。唯一能让皮埃尔体现其价值的职位是在巴黎大学任教授,人们不愿给他这个职位,却愿意给这位大师耗时巨大的次要工作。
居里夫妇集中精力为学生备课、出题、选实验项目。皮埃尔这时要教授和指导两批不同的学生。玛丽初次登台用法语授课,备课极其认真,为赛弗尔学校的女生组织实验也非常精心。她改进教学方法,授课富有创意,校长吕西安·普安加瑞感到非常惊异,向这位年轻的女教师表示祝贺。玛丽做任何事都不会半心半意。
但是,他们因此浪费了多少精力,不得不牺牲多少做真正工作的时间!玛丽每周要去赛弗尔学校好几次,她手里提着沉甸甸的皮包,里面塞满批改过的作业,有时要在路边等半个钟头,才能搭乘上慢得让人难以忍受的电车。皮埃尔要从拉赫芒德路匆匆赶往理化自然科学学部所在的居维埃路,然后从居维埃路赶回拉赫芒德路的棚屋实验室。实验刚开始不久,又得离开自己的仪器,去辅导学校里的年轻学生,向学习物理的学生提问。
他本来希望,做这份新工作能让他使用实验室,那对他是个极大的安慰。但是,在理化自然科学学部,他只得到两间一丁点小的屋子。他太失望了,竟然背弃不愿向人提要求的本性,申请一个适于工作的大实验室。结果没有成功。
玛丽后来写道:
凡提出类似要求的人,都知道会在经济上和行政上遇到多大的困难,也不会忘记为了得到一丁点利益,要写多少封申请书,要多少次找人谈话。皮埃尔·居里为此感到极为灰心丧气。
作这种努力影响了居里夫妇的工作效率,甚至影响到他们的能力。皮埃尔尤其觉得疲惫不堪,认为减少工作时间成为刻不容缓的事情。就在这个时候,巴黎大学矿物学教授出了空缺,由于他发展了物理学结晶理论,因此特别适合这个职位。他提出了申请。结果却被他的竞争者夺走了机会。
蒙田(1)曾写过:“富有才干的人若过分谦虚,则可能长期默默无闻。”
皮埃尔·居里的朋友想方设法为他争取难以得到的教授职位。一九〇二年,马斯卡教授不断鼓励皮埃尔,要他向科学院自荐,认为他肯定能成功,而这样会对他的物质生活大有裨益。
他迟疑很久,最后勉强同意了。按照当时的惯例要拜访所有院士,他觉得这既愚蠢又丢人。但是学院物理系一致支持他。这感动了他,他成了一位候选人。他在马斯卡的敦促下,他请求会见这个著名团体的每一位成员。
后来他成为名人,新闻记者便挖掘这位著名科学家的趣闻轶事。有一位记者描写皮埃尔·居里在一九〇二年五月搞的那轮拜访时写道:
……爬上楼梯,按门铃,叫人通报姓名,说明来意——这一切让这位候选人不由自主感到羞愧。更糟的是,他还得罗列自己获得过的荣誉,陈述自己的优点,吹嘘自己的科学工作,他觉得这些都不是人应该做的事情。结果,他反倒对自己的竞争对手表示诚挚的赞扬,说阿玛加先生比他居里更有资格进入学院……
选举结果在六月九日公布出来,在皮埃尔·居里和阿玛加先生两者中,院士们选择了阿玛加先生。
皮埃尔将这则消息告诉他的密友乔治·古伊:
亲爱的朋友:你的预料没错,阿玛加当选了。他得到三十二票,我得到二十票,热内得到六票。
为了这个美妙的结果,我耗时费力跑去拜访人,真觉得后悔。是物理系一致要把我推到头一名的位置,我只好顺从。
……因为我知道你喜欢听,才对你说了这么多废话,不过别以为这种小事对我有任何影响。
你忠实的朋友
皮埃尔·居里
不久,新上任的院长保罗·阿佩尔试图通过另一种途径帮助皮埃尔改善生活。这位校长就是原来玛丽·斯科洛多斯卡听课时为之着迷的那位教授。他知道居里有不屈的天性,于是为他准备了这样的方案。
保罗·阿佩尔写信给皮埃尔·居里说:
教育部要我拿出荣誉勋章提名。你的名字一定要写在这个名单中。我请求你将这件事当作对学院的贡献,准许我为你提名。我理解,像你这样有建树的人,对这种勋章并不感兴趣,但我要提出本学院成绩最卓越的人,提出在教学和科研中表现最出色的人。通过这种方式,部长可了解这些人,并了解我们巴黎大学的工作。你得到勋章后,佩戴或不佩戴当然可以随意,不过我请求你允许我为你提名。
亲爱的同事,请你原谅我如此打扰你。
你诚挚的忠实同事
保罗·阿佩尔
保罗·阿佩尔在写给玛丽·居里的信上说:
……我对李亚尔德校长多次谈到居里先生在工作中的优秀表现,谈到他的设备不足,也谈到他应该得到较大实验室的理由。校长利用七月十四日国庆授勋的机会,在部长面前谈起居里先生。部长显然对居里先生极为感兴趣,作为一个起点,他也许要通过授勋表示自己对他的兴趣。假如有这种可能,我请你利用你的影响力,劝居里先生不要拒绝。这件事情本身没什么价值,但是从实验室、津贴等因此产生的实际结果看,还是有相当价值的。
我请求你以科学和学院的最高利益着想,坚持要求居里先生允许我们为他提名。
这一次,皮埃尔·居里不愿“屈从任何事物”了。他对荣誉的深深厌恶感就足能为他此时的行为做出解释,此外,他还受到另一种感情的刺激。他认为,不向科学家提供工作所需的条件,却要给他颁授一枚珐琅质十字架,吊在一个红丝带上,作为对“优秀表现”的鼓励,这可实在太滑稽了。
皮埃尔·居里对院长的答复如下:
敬请转达对部长的谢忱,并请禀告部长,我根本没有获颁勋章的需要,不过我确实急需一间实验室。
他们放弃了过比较舒适生活的希望。既然得不到急需的实验室,居里便满足于在那间棚屋中搞自己的实验,在这间棚屋中度过的时光热情洋溢,足以安慰他们在各种方面受到的挫折。他们继续教书,这完全出于美好的愿望,并不感到痛苦。许多男孩对皮埃尔上过的课有着清晰而生动的记忆,心里怀着感激。在赛弗尔学校,许多女孩将自己对科学的热爱归功于玛丽,这位金发教师带有斯拉夫口音的科学论证如同歌唱一般动听。
教学工作和他们自己的研究工作让夫妇俩废寝忘食疲惫不堪。玛丽原先规定的“正常”生活规则抛在了脑后,她顾不得做饭,顾不得管理家务了。这对夫妇大量透支体力,并没有意识到这种行为不明智。有好几次,皮埃尔因为两腿突然剧痛,实在忍受不住,这才卧床休息。玛丽在坚强的神经支持下身体倒是没有垮。家人为她的结核病感到担心,她却以满不在乎的态度应付日常生活,结果疾病并没有把她缠住,她便认为自己的身体无比结实。但是,我们从她定时记录自己体重的小笔记本里看出,在棚屋里度过的四年里,她的体重减少了七公斤。这对夫妇的朋友们注意到她形容憔悴,脸色苍白。有一位年轻的物理学家甚至给皮埃尔·居里写信,专门请他们夫妇俩注意保重自己的身体。这封信就是居里夫妇生活中一幅令人担忧的画面,也是他们为事业做出牺牲的身体状况写照:
……在物理学会见到居里夫人,她的面貌变化大得让我吃惊。我十分清楚,她因做博士论文而过度劳累……不过,这也让我注意到,她没有足够的体力过你们二人这种纯精神的生活。我谈到的不仅是她,你也应该认为说的也是你自己。
我只想举一个例子:你们俩几乎不吃什么东西。我不止一次看到,居里夫人只吃两片香肠,喝一杯茶,就当成一顿饭。即使体格健壮的人,营养如此不足,难道不会受损害?想象看,如果居里夫人身体垮掉,你们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
她自己满不在乎或者固执己见,但这不能成为你推卸责任的借口。我料到你会说:“她不饿。她又不是孩子,哪会不知道该怎么做!”说实话,她真的不知道。她的行为就像个小孩子。我对你说这些,完全是出于朋友情谊。
你们没有留下足够的吃饭时间,而且食无定时,晚餐吃得太晚,结果胃口等待时间太长,机能减退,最后会失去正常功能的。毫无疑问,研究工作可能导致你们某一天推迟吃晚饭,但是你们无权养成这种习惯……你们不能一直像现在这样,把科学研究方面的当务之急与日常生活的每时每刻混淆在一起。这一点非常要紧。你们必须允许自己的身体有喘息的机会,吃饭前要心平气和地坐下来,吞咽的时候要慢,吃饭时要避免讨论忧心的事情,也不要谈论让精神感到紧张的事情。不要在吃饭时读物理学方面的书,也不要谈论物理学……
对别人的警告和责备,皮埃尔和玛丽天真地回答道:“可我们也会休息。我们夏天要度暑假的。”
他们的确要休假,或者说,他们自认为是在休假。遇上好天气,他们像往日那样从一个地方漫游到另一个地方。他们所谓的“休息”,就是在一八九八年骑自行车周游塞文地区。两年后,他们沿海峡岸边从哈夫赫骑往索米河畔的圣瓦莱里,然后渡海前往诺曼底岛。一九〇一年他们去了浦尔都,一九〇二去过阿罗芒奇,一九〇三去特里港,后来还去过圣特罗让。
这些旅行让他们得到了身体上的休息和精神上的放松吗?值得怀疑。该受责备的是皮埃尔,他从来是个不安分的人,在一个地方待上两三天,他就把念头转向了工作,显得魂不守舍,再也待不下去。于是他就谈起要回巴黎,仿佛责备自己似的以温和的口吻对妻子说:
“我们已经很长时间没做过任何事情了。”
一八九九年,居里夫妇作了一次长途旅行,从中得到了巨大的乐趣。这是玛丽婚后第一次回到祖国,他们没有去华沙,而是到了奥地利属下的波兰领土,去了德卢斯基夫妇正在建设疗养院的地方扎科巴纳。就在泥瓦匠干活的工地隔壁,一群亲人相聚在“埃热公寓”。斯科洛多斯基老师也赶来了,这位老人依然十分活跃,四个儿女及其四家人都来此相聚,把老人乐得跟返老还童似的。
岁月过得多快啊!当年他的儿子和三个女儿在华沙当家庭教师,到处找学生,这事仿佛就发生在昨天。而今天,约瑟夫已经成了非常知名的医生,娶了妻子,生育了孩子;布罗妮娅与卡什米尔正要建立一个疗养院;海拉任教师在逐步成就自己的教育事业,她丈夫斯坦尼斯拉夫·扎垒是一家照相企业的领导人。小女儿玛妮娅在一间实验室工作,还发表了研究报告,他以前喜欢把家里这个最小的女儿昵称作“小淘气”。
皮埃尔·居里是家族里的“外国人”,于是备受关注。他的波兰亲戚都以带他参观波兰为荣。起初,他对乡间景色没有很大兴趣,觉得只有黑魆魆的松林直插云霄,后来,他攀登了一次名叫“利茜”的主峰,这才对这座高耸的山峦诗画般雄伟的景色着了迷。夜晚,他当着全家人对妻子说:
“这个国家真美。现在我明白人们为什么热爱它了。”
他刻意用刚刚学会的波兰语说出这两句话,虽然语音很糟,但他的亲戚们都表示赞赏,玛丽露出骄傲的微笑,乐得脸上熠熠放光。
三年之后,在一九〇二年五月,玛丽再次登上返回波兰的火车,这次她心急如焚!她收到家里来信,说父亲突然生病,做手术从胆囊里取出几块很大的结石。起初,她收到几封让她感到安慰的信,后来突然接到一封电报。父亲病危。玛丽迫不及待要动身,可护照签证手续繁杂,等了好几个钟头才办好各种红头文件。两天半的旅行后她才抵达华沙,来到约瑟夫住的房子里,父亲生前曾在此居住,但她来得太晚了。
一想到再也见不着父亲了,玛丽忍不住心中的悲伤。在旅途中,她已经得知了父亲的噩耗,就拍电报乞求姐姐们推迟举行葬礼。她走进灵堂,见里面只有一具棺材和几束鲜花。她固执得要命,坚持要求打开棺木。大家只好照办。父亲面孔平静,毫无生气,一个鼻孔原来流出的血,在脸上留下一道淡淡的血痕。玛丽向父亲告别,乞求他原谅。她常常为留在法国而暗自责备自己,老人一直希望在她的陪伴下度过晚年,结果她让父亲失望了。在打开的棺木前,她默默自责,心里怀着悔恨,最后哥哥和姐姐出面干预,才终止这痛苦的一幕。
玛丽从来心怀顾虑,但她这样折磨自己并不公平。她父亲晚年生活十分快乐,而且由于她才更加快乐。一家人全都孝敬老人,斯科洛多斯基先生儿孙满堂,忘记了无所作为的沧桑一生。他一生终极的快乐源于玛丽。这个女儿发现了钋和镭,巴黎科学院的论文集里,举世瞩目的论文上签着他女儿的名字。这位物理学教师因此激动不已。他一辈子忙于谋生,从来不能专心从事研究。对于女儿的研究工作,他一步步密切注意着,心里清楚其重要意义,预料到女儿的发现必然受到全世界瞩目。不久之前,玛丽向他通报说,通过四年坚持不懈的努力,她已经得到一些纯净的镭。在他去世前六天写的最后一封回信中,斯科洛多斯基先生复述了她信中的这几个字眼,颤抖的笔迹已经与他原来漂亮规矩的字体大不相同了。他在信上说:
你制得了纯净的镭盐!要是计算一下为了得到它所花费的劳动量,这肯定是所有化学元素中最昂贵的!看来它只有理论上的价值,这真可惜。
这里一切照常。天气温和,仍然有点凉。我现在得上床了,就此搁笔。亲切拥抱你……
如果这位好老人能多活两年,得知女儿与亨利·贝克莱尔和皮埃尔·居里共同获颁诺贝尔奖,那他该有多么幸福,多么自豪啊。他的小女儿,他的“安秀佩西奥”获得了诺贝尔奖!
玛丽离开华沙时,脸色更加苍白,身体愈发消瘦了。九月份,她再次返回波兰。丧事之后,斯科洛多斯基家的“儿女们”再次团聚,这证明兄妹间的手足之情依然存在。
到了十月,皮埃尔和玛丽返回那间实验室。两人都觉得十分疲惫。玛丽一边与丈夫合作从事研究,一边撰写提纯镭的结果报告。但她缺乏热情,什么都不能激起她的兴趣了。长期以来的生活方式对她的神经系统产生了奇怪的影响。她患了轻度梦游症,到了夜晚,她会起床在房子里到处走动,自己却毫无知觉。
接下来的几年发生了几桩不愉快的事件。首先是她怀了孕,接着意外流产了。这次失望的流产让玛丽深感悲哀。
一九〇三年八月二十五日,玛丽在写给布罗妮娅的信中说道:
这次意外让我觉得难过极了,我几乎没有勇气写信告诉任何人。我本来已经觉得这是个孩子了,因此感到无比绝望,简直无法安慰自己。我求你给我写信,你是否认为这是我全身处于疲惫状态所致,我不能否认,自己没有注意保存体力。我一向对自己的身体很有信心,现在才为付出沉重代价而后悔莫及。这个孩子是个小女孩,生下来的时候还活着。我多想要她啊!
后来,从波兰又传来坏消息:布罗妮娅的第二个孩子,出生没几天就死于结核性脑膜炎。这是个男孩。
玛丽写信给她哥哥说:
德卢斯基家遇到的不幸让我难过极了。那个孩子本来就是健康的象征。如果照料如此周到的健康孩子都会遭遇不幸,别的孩子还有什么长大成人的希望呢?如今我一看到自己的女儿,就吓得发抖。布罗妮娅遭受的悲哀让我的心都碎了。
这些悲哀的事件给玛丽的生活笼罩上了阴影。另一桩痛苦更加严重,使他们的生活雪上加霜:皮埃尔病了。他常常受到剧痛的折磨,由于没有其他明显的症状,医生便笼统地称之为风湿病。那种疼痛频频袭击他,他往往一整夜痛苦呻吟,身体虚弱不堪。妻子吓坏了,只好整夜守在他身边。
尽管如此,玛丽仍然要在赛弗尔学校教书。皮埃尔也必须辅导他数目众多的学生,指导他们做实验。两个物理学家梦想得到的实验室离他们实在遥远,只好继续在棚屋里做精细的实验。
一次,皮埃尔不由露出一句抱怨,低声说了句:
“我们选择的这种生活太苦了。”
他以后再也没说过这种话。玛丽当时想表示不同意,可她也无法排除心中的焦虑。既然皮埃尔如此气馁,那他准是浑身的精力都用尽了。难道他得了什么可怕的疾病?难道可能是不治之症?难道玛丽自己能克服这种可怕的疲惫吗?过去几个月中,死亡的阴影一直在这个女人身边徘徊,一直在困扰着她。
“皮埃尔!”
这位科学家吃了一惊,扭头望着玛丽。她刚才的喊声充满痛苦,声音惊恐而压抑。
“怎么啦,亲爱的?你这是怎么啦?”
“皮埃尔……要是我们俩有一个死了……另一个也活不成……我们谁离开对方也不能活,对不对?”
皮埃尔缓缓摇了摇头。玛丽说出这番爱意绵绵的话,一时忘记了自己的使命。这让他记起,科学家无权背弃科学,那才是科学家终生的目标。
他凝视着玛丽悲哀扭曲的面孔,片刻之后,他口吻坚定地说:
“你错了。不论发生什么事,即使人变成了没有灵魂的躯壳,也必须继续工作下去。”
————————————————————
(1) 蒙田(1533—1592):法国思想家、散文家,其散文作品被认为是十六世纪法国散文登峰造极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