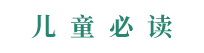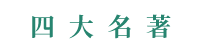第二十章 成功与磨难
每天早上,都有一个瘦削的身影走进居维埃路上那间狭窄的实验室,从衣帽钩上取下一件粗布工作服罩在黑色衣服上,马上便开始工作。她脸色很苍白,面色越来越憔悴,一头金发忽然花白了。
虽然玛丽自己并没有意识到,但是在她生活中这段阴暗的时光中,她的容貌却日臻完美。据说,人上了年纪,容貌才能定型。这句话对我母亲完全适用!玛妮娅·斯科洛多斯卡少年时期只能算是“可爱”,上大学和成为年轻妻子的时候变得十分迷人,如今她是个成熟的科学家,又饱受悲痛的煎熬,这些却将她塑造成个惊人的美女了。她的斯拉夫特征辅以脑力劳动的生活环境,根本不需要用鲜艳的色彩和愉快的情绪额外装点。四十岁以后,她性情中有了一丝悲怆的勇气,还有一种越来越明显的温柔,这些却变成她高贵的装饰了。在艾莱娜和艾芙眼中,母亲多年来一直保持着这种理想的形象,后来姊妹俩突然发现母亲变成了一个非常老迈的女人,禁不住感到恐慌。
居里夫人集教授、研究者和实验室主任数职于一身,以同样无法比拟的强度工作着。她还继续承担着赛弗尔学校的教学工作。在巴黎大学,她于一九〇八年晋升为有正式职称的教授,成为世界上第一位讲授放射学课程的教授,也是当时唯一讲授这种课程的人。她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啊!虽然她认为法国的中学教育有缺陷,但是她对这里的高等教育却真心钦佩,希望成为其中的一名大师,与她年轻时钦佩的教授齐名。
担任教授两年后,玛丽开始着手编写自己的讲义,于一九一〇年出版了一本厚达九七一页的高水平专著《论放射性》。尽管居里夫妇宣布发现镭还是不久前的事,但是在这一领域已经获得了极为丰富的知识,这本厚厚的书几乎不能将这些知识完全囊括其中。
这部著作封面上没有作者像。玛丽在封二放了一张皮埃尔的照片。两年前,由玛丽整理后于一九〇八年出版的《皮埃尔·居里作品集》上,也印着这幅照片。那是一本厚达六百页的著作。
这位寡妇为这部作品集作序,追述皮埃尔的科学生涯。她十分克制地哀悼他的不幸去世:
皮埃尔·居里去世前几年创作颇丰。当时他的知识已得到充分发展,实验技能也臻于完美。
由于获得了更完善的工作条件,他生活中的一个新时期正要开始,他令人钦佩的科学生涯本该自然延续。然而,命运多舛,我们只能在这费解的命运前低头。
居里夫人的学生人数与日俱增。一九〇七年,一位名叫安德鲁·卡内基的美国慈善家向她提供了系列年度奖学金,使她能在居维埃路的教室里多接受一些新生。这些新生有些成为大学雇用的实验室助手,有些成为义务自愿工作人员。其中有一位身材颀长天资聪颖的男孩,他名叫莫里斯·居里,是雅克·居里的儿子。玛丽对他的成功感到自豪,始终像母亲一样关怀这个侄子。一位忠实的朋友与玛丽一道负责这八到十位学生的学业,这位朋友便是居里夫妇的老合作者、一流的科学家安德烈·德比尔纳。
尽管居里夫人的健康越来越差,但她制定了一个系列研究计划,并一直贯彻始终。
她提纯了几百毫克氯化镭,并第二次确定了这种元素的原子量。在此基础上,她开始分离金属镭。在此之前,她每次制出的“纯镭”都是镭的盐(氯化物或溴化物),这是镭的唯一稳定状态。玛丽与安德烈·德比尔纳合作,终于分离出纯粹的金属镭,金属镭并不因空气作用而发生改变。这是科学上已知最艰难的操作,后来再也没有人重复做过。
安德烈·德比尔纳还帮助居里夫人研究钋及其发出的射线。最后,玛丽独自发现了一种方法,可通过测量镭的射气来测定镭的原子量。
放射疗法在普及。这一事业的发展要求将这种贵重物质的微小颗粒精确细分成很小的份额。当需要量为一微克时,天平就没什么用处了。玛丽有了个主意。她根据放射物质发出的射线强度为之“称重”。她将这项复杂的技术推向实用化,在她的实验室创立了“测量服务”,科学家、大夫甚至平民都可以拿放射性矿物来检验,领取一份标明镭含量的证书。
在她发表《放射性元素分类》和《放射性常数表》的同时,又在完成另一项具有普遍重要意义的工作:制定镭的第一个国际标准。玛丽的情绪十分激动,亲自将二十一毫克纯净的氯化镭装在一只小安瓿里,庄重地存进巴黎附近赛弗尔的度量衡标准局,作为镭的计量标准。这便是后来通行五大洲的镭标准计量单位。
居里夫妇出名后,“居里夫人”的个人声誉越来越响亮,传播速度快得像火箭。名誉博士证书、外国科学院的通讯院士证书等等接踵而至,把西奥克斯家里书桌抽屉都塞满了。可这位接受者从来没想过把这些证书拿出来展示,甚至连写个证书列表的念头都没有过。
法国对在世的伟人只有两种表彰方法:颁授荣誉勋章和科学院院士头衔。一九一〇年,法国向玛丽颁授骑士十字勋章,但她受皮埃尔·居里的影响拒绝接受。
几个月后,一些特别热心的崇拜者劝她申请成为科学院院士,她为什么没有同样拒绝呢?难道她忘记了丈夫在失败和成功时同样受辱的可怜得票数?难道她没有意识到,自己周围已经撒开一张嫉妒的罗网?
她的确没有意识到。她是个天真的波兰女人,以为拒绝第二祖国给她的这一崇高荣誉会显得自负,显得不知恩。
她的竞争对手是高级别科学家、天主教徒埃都亚·布朗利。结果,在“居里的支持者”与“布朗利的支持者”之间,在自由思想者与宗教信仰者之间,在赞成妇女入科学院当院士的人与反对这种新鲜事物的人之间,全方位的对抗爆发了。玛丽无能为力,惊惶失措地目睹着这场始料未及的争论。
几位最伟大的科学家领导了支持她的活动,其中有亨利·普安加瑞、罗克斯大夫、埃米尔·皮卡德、李普曼教授、布提教授、达尔波克斯教授。对方的阵营也准备了一种有利的防卫武器。
“妇女不能进法国科学院”,阿玛加先生带着卫道士的愤慨口吻说。八年前,就是这位阿玛加先生,在与皮埃尔·居里竞争时获胜。一些拨弄是非者跑到天主教徒一边,说玛丽是个犹太人,然后又跑到自由思想者一边,说她是个天主教徒。到了一九一一年一月二十三日投票那天,校长宣布开会时高声对看门人说:
“任何人都可以进来,但女人除外。”
一位几乎双目失明的院士赞成居里夫人进科学院,他后来诉苦说,有人当时把一张假选票塞到他手里,他险些投了她的反对票。
四点钟,记者们匆匆离席,赶去写选举失败或成功的“报道”:玛丽·居里只差一票没有当选。
在居维埃路上,实验室的助手和工人比这位候选人还着急,都在等待着选举结果。他们原以为百分之百能成功,所以这天早上买来一大束鲜花,藏在摆放精密天平的桌子下面。结果,失败让他们惊呆了。机械师路易斯·拉戈特心情沉重,把那束没用的花清理出去。年轻的工作人员们心里默默准备着安慰言辞,但是他们根本用不着说这番话。玛丽从她的小办公室走出来,对于这次挫折并不当回事,一句评论也没说。
在居里夫妇的经历中,法国对他们的态度仿佛不断受到其他国家的纠正。一九一一年十二月,瑞典科学院向这位女科学家颁发当年的诺贝尔化学奖,嘉奖她在丈夫去世后独立做出的出色贡献。从来没有哪个得奖人两次获得过这种奖赏,不但女人没有,男人也没有。
玛丽身体虚弱多病,请求布罗妮娅陪她同去瑞典。她还带了大女儿艾莱娜一道旅行。这个孩子参加了这次庄严的会议。二十四年后,在这同一间大厅里,她也接受到同一奖项。
颁奖之后,除了照例有的招待会和国王举行的晚宴外,人们还特别为玛丽组织了喜庆活动。有一个活动永远留在了她的记忆里,那是个令人喜悦的乡村庆典,几百位妇女身穿色彩鲜艳的服装,头上戴着蜡烛组成的冠冕,烛光随着舞蹈摇曳,如同一顶顶王冠在闪烁。
在公开讲演时,玛丽将人们对她慷慨表示的尊崇转而献给皮埃尔·居里的英灵。
在谈到本次讲演的正题之前,我希望指出,发现镭和钋是皮埃尔·居里和我共同研究的结果。放射性领域的几项基本研究也要归功于皮埃尔·居里,这些研究有的是他单独完成的,有的是与我共同完成的,有的是在他的学生们合作下完成的。
虽然我分离出了纯镭盐,并且确定镭是一种新的元素,但这与我们共同的研究工作有着密切联系。因此我认为,瑞典科学院授予我如此崇高的荣誉,是基于对我们共同工作的认可,也是对皮埃尔·居里表示的敬意。
玛丽做出了伟大的发现,享有全球驰名的声望,两次获得诺贝尔奖,无数同时代的人无比羡慕她,因此也有数不清的人仇视她。
恶意突然朝她扑来,想要毁掉她。巴黎掀起一股浊浪,攻击这个四十四岁的虚弱女人。她独自坚持着常人无法承受的辛劳,对这种进攻并不抵抗。
玛丽做的是男人的工作,选择的朋友和知己也都是男人。她的人格对密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对其中一位影响尤其显著。这就足够了。于是人们指责她,说一个女科学家本来应该献身工作,生活也应该矜持而有尊严,但是,近年来这个女人却变得特别可鄙,她破坏别人的家庭,有辱她的姓氏,玷污了她辉煌的名誉。
我觉得不该由我评判那些发动攻击的人,我不该说出玛丽感到如何绝望,也不该说出她如何痛苦挣扎。我们也不去提那些记者,他们在这个女人受到匿名信骚扰,公开受到暴力威胁,甚至生命都遭遇危险的时候,还落井下石诽谤她。虽然有些攻击她的人后来请求她的宽恕,流着眼泪懊悔不已,但是罪行已经犯下了,玛丽精神崩溃,几乎发了疯,差一点儿要自杀。她的身体也垮了,患了重病。
我只愿意在如林的毒箭中挑出一支稍加描绘。这其实是一支最不致命,却最卑鄙的毒箭,它随时都瞄准着她。正如在一九一一年那些痛苦的日子里,或者她的一种头衔、奖赏或荣誉受到拒绝,每逢有机会让这位独特的女人受屈辱,便有人提出她的国籍来非难她,说她是俄国人,说她是德国人,说她是犹太人,说她是波兰人,说她来到法国巴黎想以不正当手段篡夺崇高的地位。然而,每逢玛丽·居里以自己的天才为科学增添了光彩,每次她在别的国家受到前所未有的称颂,在同一份报纸上,她立刻变成了“法国的女使者”、“我国天才的最纯洁代表”、“国家的荣耀”等等,全然不提她引为自豪的波兰国籍,这同样是不公正的。
伟人往往容易受到某些人的攻击,那些人总是渴望从天才的甲胄下找到人性的弱点。若不是荣誉这种可怕的磁性吸引来同情和憎恨,玛丽·居里决不会受到如此严重的诽谤和中伤。于是,她憎恨名望又有了一个新的理由。
逆境中要靠朋友。玛丽收到几百封信,信中对她受到的磨难表示同情,也表示愤怒。这些信有些来自她的熟人,也有些是素不相识的人写来的。许多人为玛丽而战斗,其中有安德烈·德比尔纳、让·佩林夫妇、沙瓦纳夫妇、一位好心的英国朋友埃尔顿夫人、玛丽的助手和学生等等。在大学圈子里,有些几乎不认识她的人也主动帮助她,譬如数学家埃米尔·波瑞尔夫妇就是这样。他们对她的友好关怀无微不至。她哥哥约瑟夫、姐姐布罗妮娅和海拉匆匆赶到法国来帮助她。为她辩护态度最坚定的是皮埃尔的哥哥雅克·居里。
亲友的挚爱让玛丽恢复了一些勇气,可她的身体日渐衰弱。觉得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在西奥克斯与大学之间奔波了。于是,在巴黎租了套房子,地点在白求恩码头路三十六号。她打算从一九一二年一月起搬到那里去住,可她没有支撑到这个日子,十二月二十九日,人们把她送进了一所疗养院,她当时已经奄奄一息,几乎送了命。不过,她还是征服了病魔,但她的肾脏发生了严重病变,需要做手术。没出两个月,玛丽就被人用担架抬进医院好几次,现在身体极其虚弱。可她要求把手术推迟到三月份,因为她要在二月底参加一次物理学大会。
著名外科医师查尔斯·瓦尔特为她做了手术,并精心护理她,可她的身体仍然长期处于危险中。玛丽瘦得可怜,想站起来都困难。她忍受着发烧和肾脏疼痛,从不叫苦。要是换了别的女人,恐怕从此要抱病卧床了。
身体的疾患加上人们的卑鄙诽谤,她就像个走投无路的困兽,不得不到处躲藏。她姐姐为她在巴黎附近的布鲁诺地方租了一处小房子,租房子时用了“德卢斯卡”的名字。这个病人在那里住了一段时间,然后又在忧郁中隐姓埋名在图农疗养了几个礼拜。到了夏天,她的朋友埃尔顿夫人接她和她的女儿们到英国海边一所平静的房子里去住。她在那里受到了照料和保护。
就在玛丽感到前途黯淡的时候,有人向她提出一个预料之外的建议,她既感到兴奋,又觉得为难。
一九〇五年革命之后,沙皇政权逐渐走向崩溃,对俄国的自由思想作了一些让步,就连华沙的生活条件也不似原先那么严酷了。一九一一年,华沙一个相对独立而且非常活跃的科学协会将玛丽聘请为名誉会员。几个月过后,那里的学者们订立了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要在华沙创立一个放射性实验室,要迎请这位世界上最伟大的女科学家居里夫人回国领导那里的工作。
一九一二年五月,一个由波兰教授组成的代表团来玛丽家拜访。代表团还带来一封信,写信的人是波兰最著名、最受欢迎的作家亨利克·显克维支。虽然这位作家没有见过玛丽,但他在这封请求她回国的信中既对她表示出敬仰,也带着谆谆恳请的亲切口吻:
最尊敬的夫人:恳请您返回我们的祖国和我们的首都,在这里继续您光辉灿烂的科学活动。您一定明白近年来使我国的文化和科学濒临没落的种种原因。我们对自己追求知识的能力丧失了信心。我们的敌人蔑视我们,我们自己对未来也不抱希望了。
……我国的人民都钦佩您,更希望看到您在这里工作,看到你回祖国工作。这是全国人民热切的希望。有您在华沙,我们会感到比较强大,我们就能抬起在不幸中低下的头。愿我的衷心祈祷能成为现实。请不要拒绝我们向您伸出的手。
换了一个没什么顾虑的人,这该是多么好的机会啊,借此体面离开法国,不再理会诽谤,不再承受残忍的行为!
但是玛丽从来没有怨恨。她以真诚的心情急切地考虑自己的责任所在。回国这个主意既吸引她,又让她感到害怕。她的身体非常虚弱,害怕做出举家迁徙决定。此外还有一个原因:在一九〇九年,一项计划终于敲定了,要建设居里夫妇长期渴望的实验室。这时候如果离开巴黎,从法国逃走,那就等于使这个计划化为泡影,也等于扼杀了一个伟大的梦想。
这是两种互不相容的职责,这也是玛丽一生中最虚弱的时期。她疲惫不堪的心在做着斗争。不知承受了多少思乡的痛苦,也不知经过多少时日的迟疑,最终她寄出婉言谢绝华沙的信,她心里该是多么痛苦啊!不过她仍然答应对这个新实验室提供远距离指导,并由她两个最好的助手管理。这两位助手是波兰人达尼什和卫滕斯坦。
一九一三年,玛丽拖着重病的身体前往华沙,参加那座放射性实验室的落成典礼。俄国当局对她的出席故意不理睬,没有一个俄国官员参加为她组织的招待活动。如此一来,祖国同胞对她的欢迎就更加热烈。在一个挤得水泄不通的大礼堂里,玛丽平生第一次用波兰语作了科学讲演。
她在写给一位同事的信中说:
我要在离开之前尽力做出贡献。星期二,我作过一次公开讲演。我参加过各种聚会,并且还会继续参加一些集会。我在这里得到了一种善意,不应该辜负它。这个可怜的国家受到荒谬而野蛮的蹂躏,人民做出了巨大的努力,设法保卫其道德水准和知识水平。压迫者退却的一天也许会到来,人民必须坚持到那个时候。但这是什么样的生活!这又是什么环境啊!
我拜访过记忆中少年和青年时期生活过的所有地方。我又去了维斯杜拉河,还有那里的墓地和坟墓。旧地重游既让我感到甜蜜,又让我心中悲哀,可我不能不去。
有一个仪式是在工农业博物馆举行的。二十二年前,玛丽就是在这座建筑物里第一次做简单物理实验的。第二天,波兰妇女为“斯科洛多斯卡·居里夫人”举行了一个宴会。一排排客人中间坐着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小姐,老人出神地凝视着这位科学家:原来这是西科尔斯卡小姐,就是梳着金色发辫的小玛妮娅最初接受教育的寄宿学校校长。玛丽从摆着鲜花的桌子中间穿过,来到老小姐身旁,她就像当年领奖时一样羞怯,俯身亲吻老人的两颊。可怜的西科尔斯卡小姐在观众暴风雨般的掌声中流出了眼泪。
玛丽的健康逐渐好转,后来恢复了“正常”生活。一九一三年夏天,她想试试自己的体力,便背起行囊徒步在恩加迪纳地区旅行。陪她一道旅行的有她的两个女儿和她们的家庭教师,还有科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和他的儿子。在几年时间里,居里夫人与爱因斯坦之间建立起了“天才的友谊”,他们彼此钦佩,两人之间的友谊坦诚而忠实。两人有时说法语,有时说德语,喜欢不断地讨论物理学上的理论问题。
孩子们跑着跳着走在前面,对这次旅行感到极为兴奋。稍后一点,健谈的爱因斯坦兴致勃勃解释着自己一直思索的理论,玛丽的数学头脑异常杰出,属于欧洲少数能听懂爱因斯坦理论的人之列。
艾莱娜和艾芙有时听到他们说的几句话,觉得十分古怪。爱因斯坦心事重重,沿悬崖边的陡峭岩石路向上攀登,对道路的艰险却并不注意。他突然停住脚步,抓住玛丽的胳膊,大声喊道:“你明白的,我需要确切知道,电梯坠下时,乘客会发生什么事情。”
为这么滑稽的事操心!年轻人听了放声大笑,根本没想到想象中的电梯坠落会引发卓越的“相对论”。
这次短期休假过后,玛丽去了英国,参加那里举行的科学仪式。在伯明翰,她又得到一个荣誉博士学位。这一次她破例带着愉快心情忍受了折磨,后来写信把当时的情景讲给艾莱娜听:
他们给我穿了件漂亮的绿边红长袍,还有其他接受博士学位的科学家,大家都身穿这种衣裳受罪。他们对我们每人说了一段赞颂我们成就的演说辞,然后大学副校长对我们每人宣布说,大学授予我们博士学位。接着,我们都在台上就座。仪式完了以后,我们加入教授和博士的行列,大家都身穿跟我们差不多的衣服。这一切都很滑稽。我只好一本正经遵守伯明翰大学的规矩。
艾莱娜却觉得很着迷,写信给母亲说:
亲爱的妈妈:
我简直像亲眼看见了你身穿绿边红袍的模样,你穿着一定漂亮极了!他们让你保留这长袍呢,还是仅仅借给你在仪式上穿?
在法国,一场场暴风雨都过去了,这位科学家升到了荣誉的顶巅。两年以来,建筑师内诺一直在皮埃尔·居里路上分配给她的地皮上建造镭研究院。
各方面的事情安排得并不容易。皮埃尔刚去世,政府便向玛丽建议,向全国征求捐款,建设一个居里学院。这位寡妇不愿借多非纳路发生的灾难募捐,拒绝了这个建议。当局便懒得出面管这事了。但是,在一九〇九年,巴斯特研究院的院长罗克斯大夫慷慨建议说,为玛丽·居里建设一个实验室,请她离开巴黎大学,在巴斯特学院当个显赫的科学家。
巴黎大学的领导人忽然竖起了耳朵……把居里夫人挖走?不行!无论代价多大,也要把她留在巴黎大学!
后来,罗克斯大夫和李亚尔副校长达成谅解,这才解决了这场争论。巴黎大学和巴斯特研究院各出资四十万金法郎,共同创建镭研究院。该院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放射性实验室,由玛丽·居里领导;另一部分是生物研究和放射性疗法实验室,由著名医师克劳德·利高德教授组织研究对癌症的治疗和对病人的护理。这两个姊妹研究机构相互依赖,合作发展镭科学。
这个时期,人们常常看到玛丽离开居维埃路,急匆匆赶往这个布满脚手架的工地,在那里拟定计划,与建筑师争论。这个头发花白的女人脑袋里充满了现代化的新颖念头。她当然要为自己的研究工作考虑,但她更要为长远着想,想要这间实验室三十年后,甚至五十年后还能继续使用,尽管到时候她早已是尘归尘土归土了。她要求屋子建得非常宽敞,要求采用大窗户,好让实验室充满阳光。另外,她还执意要求有一个电梯,这一创意成本高昂,让政府的工程师怒不可遏……
这个永远具有农妇气质的科学家最关心花园,一定要按照自己的心意来搞。她不愿听从“节约面积”的说法,迫不及待地争取建筑物之间的每一平方英尺土地,早在建筑尚未奠定基础时,就像个鉴赏家似的选好一棵棵小树,亲自监督人们栽种下去。她对合作者们说了知心话:
“现在买下我的法国梧桐树苗和椴树苗,就是争取了两年时间。等我们开始使用这座实验室的时候,这些树都长大了,一丛丛树木就会开花。不过你们别说出去,我还没有告诉内诺先生呢!”
她那双灰色眼睛里又闪烁出了欢乐的小火花。
她亲自栽种攀援蔷薇花,挥动铁锹在没有完成的墙脚下培土,天天浇水。她迎着风直起腰来,便觉得砖石墙壁与生气勃勃的植物在一起成长。
一天,玛丽正在居维埃路实验室里聚精会神做实验,她原来的实验室工友佩第来找她,这个人情绪十分激动。物理学校也在建工作室,皮埃尔和玛丽使用过的那间潮湿的棚屋要拆掉,工人们已经挥动镐头动手了。
玛丽随昔日这位工友来到拉赫芒德路,向棚屋最后道别。棚屋还没有开始拆,人们怀着虔敬的心情,保留下皮埃尔在黑板上写的一行行字。玛丽仿佛觉得门子很快就会打开,一个高大的身影就要走进来。
拉赫芒德路、居维埃路、皮埃尔·居里路……这是三个地址,也是三个阶段。这一天,玛丽不由自主地将自己追求科学的道路回顾了一遍,她的生活中既有艰辛,也有满足。她的未来已经有了清楚的轮廓。刚刚建成的生物实验室里,利高德教授的助手们已经开始工作,到了晚上,新楼宇的窗户射出明亮的灯光。几个月之后,玛丽也要离开理化自然科学学部,把她的实验仪器搬到皮埃尔·居里路上这座建筑物里来。
这位女英雄获得如此胜利时,自己已经上了年纪,身体也不再结实,而且还失去了生活中的幸福。可这又有什么关系?她周围有了一批新生力量,朝气勃勃的科学家们都准备帮助她,大家一道奋斗。这并不算太晚。
每一层楼上都有安装玻璃的工人在歌唱,在吹口哨。楼门上方已经镶嵌了石板铭牌,上面镌刻着:镭研究院居里楼。
玛丽站在坚固的墙壁前,望着饱含敬意的题刻,不由想起巴斯特说过的话:
如果造福人类的种种发明打动了你的心,看了电报、摄影术、麻醉术等众多效果惊人的发明,如果你感到肃然起敬,如果你盼望自己国家未来在这类奇迹中做出贡献,我劝你关注这些神圣的建筑吧。人们为它们起了十分有表现力的名字,叫做实验室。让实验室大量增加吧,让这些建筑物里摆满仪器吧。它们是未来的殿堂,是财富与福利的神庙。人类就是在这些神庙殿堂中成长壮大的,就是在这里进步的。人类在这里学习,学习着阅读自然的作品、进步的作品、普遍和谐的作品,而人类自己的作品往往是野蛮的、疯狂的、具有破坏性的。
在那个美好的七月,皮埃尔·居里路上那座“未来的殿堂”最终建成了。实验室准备迎接镭、迎接工作人员、迎接这里的领导人。
可惜这个七月是一九一四年七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