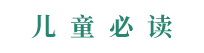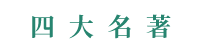第二十二章 宁静在拉古埃度假
世界重归平静。玛丽从远处注视着那些和平缔造者的努力,她的信心和希望变得越来越渺茫。
她是个理想主义者,自然而然会受到威尔逊(1)主义的影响,而且对国际联盟深信不疑。她执著地追求一种途径,希望使人类放弃一切野蛮残暴行为,同时梦想着达成一项条约,能真正消除仇恨和敌意。她曾经说:“我不能赞同把德国人彻底灭绝,应该让德国人得到一种他们能够接受的和平。”
战胜国和战败国的科学家恢复了往来。玛丽真诚地表示,她愿意忘掉过去不久的战争,不过她不肯像自己的同事那样表现出过分的友爱与热情。每逢她与德国物理学家见面前,她都会习惯地问他一句:“有没有在九十三条上签过名?”如果这个人签过,那她就会仅仅表示客气。如果这个人没有签过,她则会友好得多,与她的同行畅谈科学,仿佛战争没有发生过一样。
玛丽这种暂时的态度,表现出她极其重视动乱时期知识分子的责任和义务。她认为伟人是无法“超越战争”的:这四年,她一直忠诚地为法国服务,而且挽救了许多人的生命。但是她的一些行动反映出,她反对知识分子不该参加战争的主张。玛丽对莱茵河彼岸的作家和科学家在那份声明上签字表示谴责,后来,有些俄罗斯科学家公开赞扬苏联警察的做法,对此她也表示了谴责:有知之士不能坚定地维护人类文明,保卫思想自由,那就是背叛了自己的使命。
尽管玛丽参加了这场大战,但是她既没有变成好战分子,也没有沦落为某个宗派的成员。一九一九年,我们发现她在领导自己的那间实验室,她仍然是一位纯科学家。
她一直在盼望,期待着皮埃尔·居里路上的实验室里恢复生机。她最关心的是不要让战争期间来之不易的成果受到破坏:应该继续提供射气服务、继续向各医院分发装有“放射元素”的小试管。利高德大夫复员后,重新负责生物楼的工作,继续担任这里的领导工作。居里夫人和她的同事在物理楼继续一九一四年中断的实验,同时也开始一些新研究项目。
生活恢复了正常,玛丽也上了年纪,有更多的时间关心艾莱娜和艾芙的前途。两个女儿身体健壮,个子长得都比她高了。二十一岁的大女儿在上大学,性格冷静,有条不紊,对自己的使命从来没有丝毫的怀疑:她要成为物理学家,而且她非常明确地希望从事镭的研究。她父母取得的成就和享有的声望既没有令她气馁也没有使她胆怯。艾莱娜·居里朴实而自然地走上了皮埃尔·居里和玛丽·居里开创的道路,这一选择的确令人钦佩。她不考虑自己能否创建母亲那样的辉煌事业;也不觉得母亲的盛名对她是个重大压力。她真诚热爱科学,又具有非凡的天赋,便树立起唯一的目标:永远在她长大的实验室里工作。一九一八年,她在这个实验室里获得了“助手”职位。
玛丽的个人经历和艾莱娜幸运的例子使玛丽产生了错觉,以为年轻人可以毫无困难地在生活的迷宫中找到正确方向。但是艾芙的苦闷和不断转变令她非常不安。她对孩子们的自由意愿有一种大度而且过分的尊重,同时对她们的智慧估计过高,这使她没有在艾芙身上行使自己做家长的权力。她原本希望既有理智也有天赋的艾芙能够成为一名医生,研究镭在医学方面的应用。然而,她并没有强迫艾芙走这条路。她怀着一种不知厌倦的理解,支持着这个女儿的种种反复无常的计划。看到女儿学习音乐,她也感到十分欣慰,任凭女儿自己选择老师和学习方法……这个孩子被自己的犹豫不决所害,而她却给予她过多的自由。如果得到严格的指导,她本来可以有更好的发展。可是她怎么能发现自己的错误呢?难道她有一种不会出错的天赋,能引导她冲破重重障碍,走上命运的坦途吗?
她悉心慈祥、毫无偏袒地关心着自己这两个迥然不同的亲生女儿。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她都是艾莱娜和艾芙忠诚的保护者和热心的同盟者。后来,艾莱娜结了婚,有了自己的孩子,玛丽对这两代人都给予了慈爱和关心。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玛丽写给艾莱娜和弗雷德里克·若里奥—居里的信中这样说道:
我亲爱的孩子们:
祝你们新年快乐,也就是祝你们在新的一年里身体健康、心情愉快、工作顺利。在新的一年里,希望你们天天都快乐,不要等到日子过去后才能体会到其中的乐趣,也不要希望快乐只能在未来发现。人老了就会感到享受现在的可贵:能够享受现在是一种可以与获得天恩媲美的宝贵天赋。
我也很想念你们的小海琳,也祝她快乐。看到这个小家伙一天天在成长,真是令人感动。现在她满怀信心地期待你们能给予她一切,而且坚信你们能够使她免于各种痛苦的侵扰。有朝一日,她会明白其实你们没有这么大的力量,虽然所有的家长都希望能为自己的孩子做一切。家长至少应该努力给孩子们一个健康的体魄,让他们在爱的氛围中度过一个宁静的童年,尽可能长地让他们保持自己美好的信心。
一九一九年九月三日,玛丽在写给两个女儿的信中说:
……我常想到这一年要面对的工作,也常常想到你们俩,想到你们带给我的甜蜜、喜悦,以及对我的关心。有你们俩,我真是幸运。我希望能和你们一起过上几年舒坦的日子。
不知是令人心力交瘁的战争后她身体有了好转,还是人上了年纪心态渐稳,玛丽到了五十多岁后变得平和了许多。悲伤和疾病放松了对她的折磨,岁月冲淡了往日的痛苦:玛丽虽然没有再次找到幸福,但是她学会了热爱日常生活中小小的喜悦。艾莱娜和艾芙是在永远与病魔作斗争的母亲身边长大的,现在忽然发现母亲成了她们的新伙伴,虽然面容苍老,却有一副年轻的身心。艾莱娜是一个不知疲倦的运动者,她鼓励母亲参加运动,陪她一起徒步远足、滑冰、骑马,甚至有时还去滑滑雪。
那年夏天,玛丽去布列塔尼看望两个女儿。母女三人在拉古埃这个不受外界打扰的小村子里,度过了一个神仙般的逍遥假期。
这个小村落位于海峡岸边,邻近巴安波。居民只有水手、农人和巴黎大学的教授们。拉古埃是历史学家查尔斯·塞诺博斯和生物学家路易斯·拉皮克在一八九五年发现的。大学圈子的人认为,其重要性简直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不相上下。一个诙谐的记者给学者们的这块聚居地取了个别名,叫做“科学港”。居里夫人来这里的时间比较晚,她先是住在当地老乡家,后来又租了一座别墅,最后索性自己盖了一座别墅。她选择的地点位于荒野上,那里偏僻荒凉,面对着平静的大海,海面上还点缀着大大小小的岛屿,这些岛屿挡住了外海的海浪对海岸的冲刷。她对灯塔情有独钟;无论是她在夏天租过的别墅,还是后来自己盖的房子,外表看起来都非常相似:狭长的房屋坐落在一片空旷的地面上,房间布局欠佳,几乎没有什么家具,不过风景却非常壮观。
每天清晨,玛丽只能遇到不多的几个过路人,包括有些驼背的布列塔尼妇女、行动缓慢的农民、一笑就露出龋齿的儿童,他们都会大声地和她打招呼:“早上好,居——里夫人!”布列塔尼口音拖长了音节。哦!这简直是奇迹!玛丽并没有转身逃走,而是微笑着用同样的口气回答:“早上好,勒高福夫人……早上好,甘丹先生!”如果她认不出跟她打招呼的人,就难为情地简单说一声:“早上好!”本地人只有在仔细思量后才会用这么平静的口吻跟人打招呼,这是彼此平等的人相互问候,其中既没有鲁莽也没有好奇,只有友好。他们对玛丽的尊敬不是因为镭,也不是因为“她的名字在报纸上出现过”,而是经过两三个季节相处之后,那些把头发紧紧塞在白色尖顶帽下的农妇把她当成了自己人。
居里夫人的房子和本地的其他建筑别无二致。拉古特最有名的一座房子位于聚居区中心,这是一座低矮的茅草别墅,五叶地锦、西番莲和灯笼海棠一直攀援到屋顶上。在人们心目中,这房子简直是一座宫殿,在布列塔尼方言里,这座别墅被叫做“达山维昂”,意思是“小果园”。达山有一个位于斜坡上的花园,花园里的花草没有经过人为的设计,却自然形成一垄垄色彩夺目的彩纹。只要不刮东风,这里的房门总是敞开的。房子里住的人已经七十岁却仍然精神勃勃,他名叫查尔斯·塞诺博斯,是巴黎大学的历史学教授。这位老人身材不高,有一点驼背,但是为人十分热情,他总是穿一身带细黑纹的白色法兰绒西服,衣服已经发黄,上面还打着补丁。当地人都称他为“塞诺先生”,他的朋友则管他叫“船长”。他的魅力和他受人尊敬、爱戴和亲近的性格特点,都无法用言语表达。这个老单身汉是所有男人的好朋友,而且和他关系密切的女人比任何土耳其总督的妻子都多:他总有三四十个女伴,年龄从两岁到八十岁的都有……
玛丽沿着一条俯瞰拉纳依海湾的陡斜的小径下山朝达山走去。房前已经聚集了十五名成员,他们在那里踱来踱去,等着坐船上岛。居里夫人的出现没有在这个由移民和流浪者组成的人群中引起什么反应。查尔斯·塞诺博斯迷人的眼睛藏在近视眼镜后,亲切友善却又不拘小节地向她打招呼:“啊!居里夫人来了!您好!您好!”有几个人也跟着说您好,然后玛丽加入了这个群体,在地上坐下来。
她头戴一顶洗旧了的亚麻帽子,身穿一条旧裙子和一件结实的软毛法兰绒厚呢短大衣,这件大衣是村里的女“裁缝”伊丽莎·莱夫按照一个不分男女、不管是学者还是渔夫都合适的样式做的。她光着脚,穿了一双凉鞋,面前放着一个包,这个包和另外那十五个放在草地上的包看上去非常相似,里面装着一条浴巾和一件泳衣。
要是一个记者突然置身于这一群平静的人们中间,他肯定会欣喜万分。他必须得格外小心,不要踩到在草地上懒洋洋躺着的法兰西科学院的院士身上,或者是踢着一个诺贝尔奖得主。这里的名人不胜枚举……如果你想找人谈物理,这里有让·佩林、玛丽·居里、安德烈·德比尔纳、维克多·奥格尔。谈数学和微积分?这里有埃米尔·波莱尔,他披着浴袍,看上去却像身穿皇袍的罗马皇帝。谈生物、天文物理?路易斯·拉皮克和查尔斯·默汉都能回答你的问题。至于魔法师查尔斯·塞诺博斯,这个地方很多小孩都心怀恐惧,彼此私下说:“他知道发生的一切”……
不过在这个学者云集的聚会中最奇妙的事却是这里从来没有人谈论物理、历史、生物和数学。在这里尊敬、等级,甚至合乎礼仪的规范都被人抛在脑后。人们不再有师徒之别、长幼之分,而是分成四种:“庸人”,指那些不请自来、留在这个聚会中的陌生人,这些人要尽快被清除出去;“大象”,指那些在航海生活中没有天赋的人,留在团体中只为当作作取笑对象;“水手”指的是那些配得上此称呼的拉古埃人。最后一类是那些高级水手、熟悉海湾水流的技术专家,以及行船划桨的能手,这些人被称为“鳄鱼”。居里夫人从来都不是“庸人”,不过她也不奢望获得“鳄鱼”的称号。她做了不长时间的“大象”,随后就成了一名“水手”。
查尔斯·塞诺博斯清点完信徒人数,发出开船信号。艾芙·居里和让·莫兰这两个当值水手从停泊在岸边的两只帆船和五六只划艇中解开了“大船”和“英国船”,并把它们划到岸边,这里参差不齐的岩石形成了一个天然的小码头。那些航海家们已经等在了岸边。塞诺博斯用欢快急促、又带些讽刺的语调喊道:“上船!上船!”当船上坐满了乘客后,他又喊:“谁来划船呢?好吧,我划尾桨,居里夫人划前桨,佩林和波瑞尔划侧桨,弗朗西斯掌舵。”
这些可能难住大多数知识分子的命令在这里却立刻得到执行。四个桨手全都是巴黎大学的教授和名人,他们各就其位,听候年轻的弗朗西斯下命令,因为他负责掌舵,所以权力最大。查尔斯·塞诺博斯划下第一桨,然后为其他船员定下了节奏。在他身后的让·佩林开始用力划桨,他的力气太大,船都开始打转了。佩林身后是波莱尔,再后面是划前桨的玛丽·居里。大家都有节奏地喊着号子。
阳光洒满海面,这只白绿相间的小船在水面上平稳前进。年轻舵手严厉而公正的批评打破了寂静:“二桨没用力!”(埃米尔·波瑞尔试图否认,但很快又放弃了。不再偷懒,用力划桨。)“头桨没跟着尾桨!”(玛丽·居里一阵忙乱,纠正了自己的错误,重新跟上节奏)
查尔斯·莫兰夫人用她那优美热情的声音带头唱起《船歌》的前几句,后面的乘客很快都跟着一起唱起来:
我的父亲盖了一座房
(划呀划呀,划你的桨!)
有八十个年轻的泥瓦匠……
缓慢、有节奏的歌声夹杂在一缕代表着好天气的西北风中,飘向在海湾另一面航行的第二只船“英国船”,那只船上的船员也唱起他们那三四百首特有曲目中的一首。查尔斯·塞诺博斯会把这些歌教给每一个拉古埃的新成员。
两三支歌唱完后,这组三人桨手累了。舵手看了看表,然后喊道:“换班!”他不管桨手们是否感到疲惫,只是按规定从出发已经过去了十分钟,所以该换班了,于是玛丽·居里、贝汉、波莱尔和塞诺博斯把位置让给另外四个高等学府的成员。要划过海峡湍急的水流,到达紫色的维拉斯山岩,就必须换一组船员。拉古埃人几乎每个早晨都会到这个荒弃的海岛去洗海水浴。
男人们在空船附近满是棕色海藻的岸上脱衣服,女人们则到一个满地水草、表面光滑的角落里去换衣,这个角落从一开始就被叫做“女更衣室”。玛丽穿着黑色的泳衣,和第一批人朝大海走去。海岸很陡峭,人一跳下去就不见了。
玛丽·居里在维拉斯岩凉爽清澈的海水中游泳的姿势十分优美,那是我对母亲最愉快的回忆之一。她不用女儿和同伴喜欢的“自由式”。经过艾莱娜和艾芙的系统训练,她学会了一种手臂出水的姿势,再加上她天生的优雅,她的游泳姿势非常优美。你会忘记她藏在泳帽下灰白的头发和沧桑的面容,只会去欣赏她那和少女一样苗条、柔软的身体、白皙美丽的胳臂,还有活泼迷人的姿势。
居里夫人对自己的灵活性和在游泳方面的天赋尤其引为自豪:她和巴黎大学的同事之间暗中进行体育竞赛。玛丽观察着其他科学家和他们的妻子在维拉斯岩小海湾里畅游,有的采用标准的手臂出水式,有的虽然也在打水,却在原地漂浮,并不前进。她精确地计算着对手游出的距离,虽然并不公开提出比赛,她却开始训练自己打破其他教授的游泳速度和距离。她的两个女儿既是她的教练,也是她的知己。
玛丽有时会说:“我觉得我能比波莱尔先生游得好。”
“哦,好多啦,妈……他没法儿跟你比!”
“今天让·佩林游得不错。但你记得吗,我比昨天游得远多了。”
“我看见你游了,挺好的,比去年进步大多了。”
玛丽喜欢听这些赞扬,她知道这些话说得没错。虽然已经五十多岁了,但她却是她那辈人里游得最好的。
游完后,她就一边晒太阳暖暖身子,一边吃点干面包,等待着返航。她会发出愉快的感叹:“真舒服!”或者看着动人的岩石、天空、海水、景色,赞叹道:“真美啊!”在这里聚会的人们只愿听这句评价,这是对拉古埃最中肯的简短评价。大家都认为这里是世界上最美的地方,这里的海水最蓝——蓝得就像地中海的水,这里的环境最宜人、更富于变换,但谁也不说这些,而且谁也不会说拉古埃有多少科学奇才。只有“庸人”才会以充满诗情画意的语调赞美这一切,即使如此在遇到人们的一致嘲笑后,他们也就很快停止了这样的赞美。
中午时分,潮水退了,两只船在“安特汉海峡”里小心穿过,两边一片片的水草,像是湿漉漉的牧场。这是第一千次了,乘客们在同一个地方,完成了同一航程后,同一只船又因落潮被困在那里,要长达四个小时,船上饥饿的船员在水草中寻找小鱼和贝壳。一首歌接着一首歌,一拨水手接着一拨水手,最后终于回到了达山附近的岸边。现在上岸的地方算不得码头,只是退潮后的海藻滩。玛丽脱了鞋,一只手提起裙裾,另一只举着她的凉鞋和泳衣,勇敢地迈进没到脚踝、散发臭气的黑泥地里,朝一块干地走去。如果有哪个拉古埃人看她上了年纪,提出扶她一把或者帮她拿包,她都会感到吃惊,而且拒不接受。这些人不需要互相帮助,他们的第一条规则就是:“管好自己!”
这群水手解散,各自去吃午饭。下午两点他们会再次聚集在达山,乘坐艾格朗狄娜号游艇,做每日的例行航行。这艘扬着白帆的游艇是拉古埃的象征。这一次居里夫人没有同去,懒洋洋待在帆船上让她感到厌倦。两个女儿把她一个人留在她的灯塔里,她要么修改一些发表的论文,要么拿出工具、铲子和修建花木的剪刀,去修剪花木。在神秘的园艺劳动中,由于要跟荆豆和荆棘搏斗,她浑身被刺得出了血,腿上被划出一道道的口子、沾满泥土的双手到处都扎着荆棘。如果哪天受的伤仅此而已,那还算是幸运。有时,艾莱娜和艾芙会发现她们富有魄力的母亲扭伤了脚踝,或是一根手指几乎被锤子彻底砸碎。
快到六点的时候,玛丽下山来到海边,再洗一次海水浴,然后穿好衣服,走进达山那扇永不关闭的大门。在冲着海湾的大窗前的扶手椅上,坐着一位年岁很大、非常睿智、形容优雅的老妇人,她就是玛丽埃尔夫人。玛丽埃尔就住在这座房子里,每天晚上她都坐在这里等候航海家们归来。玛丽和她坐在一起,等着艾格朗狄娜号的白帆出现在被斜阳镀成金色的海面。上岸后,所有的乘客都沿着小径向上走。艾莱娜和艾芙就在其中,她们的手臂被晒成了古铜色,身穿廉价裙子,头上插着从查尔斯·塞诺博斯从花园采来的石竹花,根据一条约定俗成的规矩,每次出发前,查尔斯·塞诺博斯都会送花给她们戴。从她们神采飞扬的眼神中就知道她们还陶醉在去特利鄂河口或到默代岛的航行。在那里浅浅的草丛中,大家兴致勃勃地玩起了“俘虏”的游戏。包括七十岁的老船长在内,每个人都加入游戏中,这时,文凭证书全不算数,甚至诺贝尔奖也算不得什么。跑得快的科学家还能维护自己的特权,但是那些行动不那么敏捷的人则必须忍受双方“首领”的处置,在交换俘虏的时候,他们的待遇更是如奴隶一般。
那种在水中和风中半裸的幼稚表现或原始传统后来成了一种时尚,从最富有到最贫穷的各阶层人物都沉迷其中。但是在战争刚刚结束的那几年,这种做法让不了解的人们感到震惊,也引来了批评。在这种时尚出现前十五年,人们就已经发现海滩生活、游泳比赛、日光浴、荒岛野营这些宁静而朴素的运动。人们很少在意自己的形象:一件已经缝补过一百次的泳衣、一件短大衣、两双凉鞋,再加上家里的两三件棉布衣服,就是艾莱娜和艾芙衣柜里全部的夏装。后来,“庸人”占据了颓废的拉古埃,到处一派可恶景象,突突冒烟的摩托艇破坏了拉古埃的诗情画意,这里也头一次出现了卖弄风情。
吃完晚饭,居里夫人披上那件已经穿了十五年或二十年的蓬松斗篷,活像个僧侣。她搀着两个女儿的胳臂,迈步出发。沿着黑暗中的小径,她们三人来到了达山——从来都是在达山!在达山那间公用的屋子里,拉古埃的人一天内第三次聚集在一起。他们围在桌子前玩“字母”游戏。玛丽最擅长玩从袋子里抽出写着字母的纸条,然后拼成复杂的词。她总是获胜,所以两边都抢着要她。其他人则围在煤油灯下看书或下棋。
过节的时候,业余作家兼演员表演猜字谜、歌舞,还有赞美这一季中英雄事件的活报剧:两只船上的船员进行激动人心的比赛、一批异常兴奋的技术专家通力合作冒险挪动阻碍登陆的巨石、受到大家一致埋怨的东风搞的恶作剧、悲喜剧式的沉船、幽灵般的獾犯下的罪行,因为人们指责它定期去破坏达山的菜园……
灯光、歌声、孩子气的笑声、宜人的宁静,在年轻人和他们的长辈之间建立起无拘无束的伙伴关系。这是一种几乎没有什么事发生、不需要付出、天天都差不多的生活,但它却在玛丽和她的两个女儿心中留下了最深刻的回忆。虽然环境简朴,却让她们时刻体会到一种奢侈感。在布列塔尼的这个小村庄里,巴黎大学头脑敏锐的运动家们享受着海上生活的乐趣,百万富翁在任何海滩也享受不到这么生动、罕有、微妙的乐趣。这些经历只不过发生在一个可爱的小村庄里,能够获得如此惊人的成就,自然该归功于那些每年相聚在此的科学家们。
写这本传记的时候,我多次问自己,如果读者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想起他们以前读过的其他内容,会不会停下来,带着讥笑对自己说:“天哪,他们这些人可‘真好’!心地正直、富于同情、充满自信!”
不错,这本书里是有很多“富有同情心的人”。这不是我编造:确有其人,而且他们就是我描述得这个样子。那些笔调晦涩的小说家,从看着玛丽出世,到陪伴她度过一生中最后时光的同伴们身上实在挖掘不出他们感兴趣的素材。斯科洛多斯基一家和居里一家真是两个奇怪而与众不同的家庭,父母和孩子们之间没有怨恨,人们之间只有友爱,没有人在门缝里偷听别人讲话,没有背信弃义、没有争夺遗产、没有相互谋杀,人人都诚实可信!这群法国和波兰大学教授是一群奇怪的群体,他们也像普通人一样不是完美的,但是他们都全身心地致力于一个理想,这个理想不会因为他们经历了痛苦或被人出卖而改变……
我已经把我们在布列塔尼最快乐的时光描绘出来。有人可能觉得难以置信,这些愉快的假期里竟然没有势利举止,也没人闹意见。然而在拉古埃,即使是目光最敏锐的观察者也难以把最伟大的科学家和最普通的研究人员、最富有和最贫穷的人区分开来。在布列塔尼的阳光下和海浪中,我也从来没有听人谈论过钱。我们的长辈查尔斯·塞诺博斯给我们上了最富有智慧的一课:他从来不说自己是理论或学说的带头人,这位慷慨的老人认为他的财富就是我们的财富。那座大门永不关闭的房子、艾格朗狄娜号游艇、划艇一直都属于他,可是这些也属于大家。点燃蜡烛的灯笼在他房里挂起,舞会开始举行的时候,手风琴演奏出波尔卡、兰谢舞、布列塔尼民间舞曲,仆人、主人、法兰西科学院院士、农夫的女儿、布列塔尼水手和巴黎人都混在一起,相拥而舞。
遇到这种场合,我们的母亲会在一旁静静地观看。她的朋友知道她性格中羞怯、拘谨的弱点,他们总不忘记告诉她艾莱娜的舞跳得多么好或是艾芙穿的裙子多么漂亮。听到这些,玛丽·居里那张疲惫的脸上会突然出现一个天真的微笑,美丽而自豪。
————————————————————
(1) 威尔逊:Wilson,(Thomas)Woodrow(1856—1924),美国第二十八任总统(1913—1921)。